医疗保健
Review新旧(与旧新)医学模式:四十年来在生物医学 与心理社会对健康与疾患理解之间的探索
医疗工作可被理解为医生为帮助寻求医疗照护的人而采取的一系列实践(如倾听、提问、诊断或 推荐治疗)。这类医疗工作的核心在于对“疾病”和“疾病”的定义,这两个术语源于人们对“健康 不良”不同的理解。
尽管“disease”一词通常具有严格的生理学定义,而“illness”一词则通常根据人们对于“ill health”的人类体验来定义,其定义中包含了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两个方面。正如艾德勒[1]所描述的:
“一个人可能患有疾病,但自己却 unaware,并且行为上也没有表现出异常;也有可能人们在没有任何客观可验证的疾病证据的情况下,仍感觉和/或表现出生病的状态。在前一种情况下,虽然可能存在疾病,但没有疾病(illness);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确实存在疾病(illness)”。 (p. 723)
医疗工作的对象如何被概念化(即,以疾病或疾病来表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一定义对于理解与该工作相关的责任的边界和范围至关重要。
因此,若将医疗工作的对象以“狭义定义”界定为疾病——即严格关注有机功能障碍——则将转化为一种仅关注疾病物理方面的医学。在此意义上,疾病是一种生物医学概念。另一方面,若将医疗工作的对象以“广义定义”界定为疾病——即关注患者的生活世界——则将转化为一种将临床注意力导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医学,能够从容应对健康与疾患、健康状态与患病状态之间的界限因文化、社会和心理因素而变得模糊这一观念[3]。
本文旨在概述这些概念性方法在哲学上和实践中对医疗工作性质所产生的相互作用。我们首先讨论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在医学中的兴起,这是为了挑战并拓展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型。接着,我们总结了与该模型相关的主要争议和批评,并阐明其当前的相关性以及对该模型的应用情况,最后结合本期特刊的主题——青少年健康与医学,提出一些结论性评述。
问题质疑生物医学方法:医学中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兴起
在1960年至 1980[2,3,5–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乔治·恩格尔对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医学模型——生物医学模型——提出了具有影响力的质疑。他阐述了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并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医学模型——即恩格尔本人所称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3,8]。
在恩格尔提出批评之后,认为“可通过可测量的生物学(躯体)变量偏离正常值来充分解释疾病”的传统生物医学方法,其框架内并未为疾病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维度留下空间。恩格尔指出,这导致了一个根本性的悖论:“一些具有阳性实验室结果的人被告知需要治疗,而实际上他们感觉相当良好;而另一些感觉不适的人却被断定为健康”。并进一步阐明:
“现有的生物医学模型已不足够。为了提供理解疾病决定因素的基础,并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和医疗护理模式,医学模型还必须考虑患者、他[sic]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为应对疾病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设计的补充体系,即医生角色和医疗保健系统。这需要一个生物心理社会模型”。(p. 132)
换句话说,恩格尔提出在不牺牲生物医学方法优势的前提下,拓宽生物医学方法以纳入心理社会因素[7],从而使“患者将继续从疾病角度得到护理,同时心理和社会信息在护理过程中也将被赋予同等重要的地位”[9]。
在此过程中,卫生专业人员应能够评估所有致病因素,同时认识到某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有些甚至只是疾病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病因),而不是仅仅优先考虑生物因素[2]。鉴于此,恩格尔指出,基本专业知识和技能应涵盖社会、心理和生物领域,因为医疗决策和代表患者采取的行动涉及这三个领域[3]。
恩格尔的提议在理论上受到一般系统理论[10,11],的启发,该理论基于以下观点:从物理学中可辨识的最小系统到宇宙中最大的系统,所有实体(系统)在各个层面上都通过持续反馈回路[9]在结构和功能上相互关联。恩格尔认为,这种概念性方法非常适合他所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概念,并有潜力缓解整体论与还原论二分法,同时促进跨学科交流[3]。
通过将这种推理应用于医学,恩格尔将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定义为涵盖每个人所经历的人类自身以下和以上各层面的信息——即卫生专业人员力求整合来自人类/心理层面的数据、来自生物层面(以下)的数据以及来自社会层面(以上)的数据,以构建每位患者的生物心理社会描述(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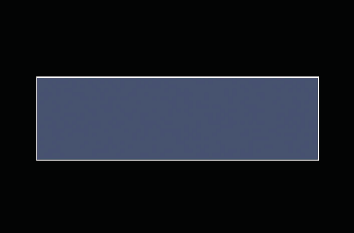
根据这一框架,必须承认层级中的每个层面都按照其独特的系统运行(例如,生物层面的组织和器官;心理层面的感知和体验;社会层面的意义赋予);然而,正是这些系统的整合对于理解患者的生物心理社会故事至关重要。因此,患者与卫生专业人员之间的沟通成为整合各个层面、理解疾病和求助行为的根本基石[9,12]。
鉴于恩格尔的提议具有理论依据,他还指出,随着后续的实证支持,该模型不仅有可能转化为更具人道关怀的医疗实践,还能使医学更加科学[9]。然而,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有潜力带来更具人道关怀和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但其兴起也伴随着一系列反复出现的批评与争议,包括该模型是否适合进行科学探究,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探讨这些问题。
医学中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主要争议和批评
继史密斯等人[9],之后,对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主要批评可分为三大类,这些类别相互重叠:
-
该模型定义过于模糊,因此无法进行检验 。一些作者指出,恩格尔最初提出的该模型的一个核心局限在于其概念发展不足[13,14]以及缺乏操作化[15,16],,这就导致该模型尚不具备通过经验验证的条件。一些作者如麦克拉伦[17]甚至认为,由于该模型不符合“模型”的通常定义——即作为可被经验验证、具有预测性和/或解释力的思想或理论的正式运作表示——因此不能将其称为“模型”。
-
该模型的范围过于笼统,无法高效地付诸实践 。其他作者强调,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表述在其范围上过于笼统,为卫生专业人员提供的指导有限[16],并引发了如何在缺乏相应标准的情况下选择性应用该模型以定位和明确相关患者信息的问题[18,19]。这可能导致大量松散相关的生物心理社会数据,使该模型在实际中针对个体患者的应用变得过于耗时和低效[20],,以致一些人质疑“在以包容主义对抗还原主义时,是否可能存在收益递减的临界点”[21]。
-
该模型未包含识别相关生物心理社会数据的方法 。一些作者指出,该模型强调了获取生物心理社会信息的必要性,但未提供任何方法学指导来协助这一过程[17]。在此背景下,批评者还指出,该模型并未说明应优先考虑哪个分析层次(生物、心理或社会)以及何时进行优先选择[19],,并且由于通常无法确定哪种因素最终导致特定病情,所有分析层次通常并存,临床医生只能自行选择看似最有效的层次[22],,而缺乏共同的依据来解释为何某位临床医生会选择这一方向而非另一方向[23]。
与此同时,包括大多数批评者在内的多位作者指出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在最初提出时存在的缺陷,并且多年来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
例如,施瓦茨和威金斯[18]提出了一种现象学模型,通过关注基本的‘理解的必要性’(即医生‘理解患者’的需求)来应对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弱点’,他们认为这强调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对医学科学的相关性’。
后来,福斯和罗滕伯格[15]提出,恩格尔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及其局限性/批评)应被视为从与生物医学模型相关的各种妥协向一个更综合的模型过渡的过程,他们随后提出并称之为‘信息医学模型’[15]。
然而,医疗工作中采用生物心理社会方法的理念似乎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共鸣,无论对新模型的批评或呼吁都未能掩盖恩格尔提议的吸引力。因此,无论该模型本身存在多少‘缺陷’,这种既能改进又不脱离传统生物医学方法的生物心理社会方法理念,引起了医学界各个领域的共鸣,这些领域希望医疗实践能够基于对健康与疾患更为全面的理解,并更贴近寻求医疗服务者的实际体验[24]。尽管存在诸多批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仍持续影响着医疗实践、教育和研究的核心方面。
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在当前实践、研究与政策中的相关性
尽管自生物心理社会模型进入医学界的主流讨论以来,人们对其不断提出批评,而且在实践与研究中对健康与疾病的身心社会理解的采纳在历史上也明显不均衡[25],,但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基本原则 increasingly 在指导和政策文件中得到呼应。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健康概念本身已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发生转变
从“没有疾病”这一定义转向基于更广泛的心理社会健康与疾患理解的更全面的认识。
同样,针对恩格尔最初提出的该模型所存在的核心问题和局限性,越来越多的研究在“解决方案”的框架下进行探讨,旨在对该模型进行补充或完善,而非取代生物心理社会模型[26]。例如,赫尔曼[20]提出,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催生了一种过渡性的、更具实用性的模型(分裂模型),这种模型“将心理社会因素降级为医生工具包中的又一个工具”,但却使卫生专业人员在实践中能够实现“生物心理社会”式的思维。孔托斯[21]认为,当代医学的复杂性并不适合依赖单一模型。其他学者则从“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多种贡献,[24],包括可教授的“思维习惯”,有助于在生物心理社会理念与临床现实之间建立切实联系;[27]“补充”[19]以及实现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实现方式”;[28]在实践与研究中连接并更好整合其三个分析层面的“策略”;最近,史密斯等人[29,30]通过回答以下问题,提出了一种更全面的“解决方案”:卫生专业人员在特定时间点为个体患者提供照护时,究竟应如何高效地识别关键的生物心理社会数据?个体患者?
这一提议本质上是对上述三个核心批评的方法论回应,认为如果能够提供“一种可重复的方法,持续识别每次就诊时定义BPS[biopsychosocial]模型所需的、相关的生物、心理和社会信息”,就能使该模型具备科学性,并推动临床、教育和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改进。在史密斯等人看来,view,这种方法应聚焦于每次临床接触中最重要的生物心理社会数据来源,即医学访谈。因此,他们建议通过整合两种基于证据的、行为定义的以患者为中心的访谈方法——“整合的以患者为中心和以医生为中心的访谈模型”和“四种习惯访谈模型”,来实现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操作化。这些方法已知能够“产生与疾病、个人/社会及情感高度相关的信息”,而非所有生物心理社会数据[9],并且已被随机对照试验证明与有效且高效的学习[31,32]以及积极的健康结果[33,34]相关联。通过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提供一种方法,将恩格尔最初提出的通用模型转化为适用于每次临床接触的具体模型,从而将该模型转变为一种基于证据、定义一致的干预手段,有望解决其核心缺陷。
同样,医学教育领域的辩论和变革也反映了这一趋势[35],人们呼吁改革医学教育,将主要以生物医学为重点的课程转变为更具包容性的课程体系,同时纳入行为与社会科学的学习内容,使医学教育者能够恰当地应对未来医学专业人员对提升心理社会能力的需求[36–38]。
考虑到类似的趋势,英国的国家健康与护理卓越研究所或美国的医学研究所等官方机构已承认,有必要通过实施更多且更完善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实践,来关注患者健康问题的心理社会层面,以此提高医疗质量[39–41]。然而,正如韦德和霍利根所指出的[42],,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对医疗服务的更大规模组织、资金支持和委托管理影响甚微。
因此,现在更需要将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应用于医疗保健管理,以应对该模型在实践与研究中的日益广泛应用[42],,其中关于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应用和使用已有越来越多的报道——最近发表的实例涵盖心脏病学[43]、肿瘤学[44],、普通儿科学和内科学[45],、骨科[46],以及妇产科[47],等多个领域,许多其他领域也已尝试实施并评估生物心理社会模型[48,49]。
方法与学科的问题:通过青少年医学视角看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未来
尽管在临床实践和研究中,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实际应用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和新出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但其持续的哲学和政治推动力正在转化为医学各个领域的越来越多实例。这些实例已经为回应先前提出的问题而进一步发展生物心理社会模型铺平了道路。
其中一个领域是青少年健康与医学[45,50,51]。为年轻人提供卫生服务是一个特别好的范例,可用于审视与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实际实施相关的当代挑战。首先,青少年医疗保健从历史上就倾向于采用更全面的生物心理社会理解来对待健康与疾患:其核心原则“基于临床互动中的生物心理社会方法”[52],,旨在“在信任与保密的氛围中提供全面而彻底的身体和心理社会评估与治疗”[53],以更好地满足青少年和年轻成人发展需求的复杂性及内在整体性[54]。其次,由于年轻人的年龄范围——即10至24岁[55]——使青少年服务正处于儿科和成人护理的交汇点,这为在更广泛的医疗保健系统组织背景下探讨这些挑战提供了独特的机会,特别是对于那些患有慢性疾病、需要从儿童导向的护理过渡到成人导向的护理的人群而言[41]。
然而,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以更好地整合健康与疾患的生物医学和心理社会层面仍然具有挑战性,即使在青少年医学等领域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中,青少年健康专家所倡导的该模型往往与使用卫生服务的年轻人的实际体验相去甚远,并且临床医生在医疗保健的生物医学和心理社会层面的整合上也存在着不同方法[57]。
然而,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证据体系有助于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特别是,通过整合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基于证据的方法学进展以及特定疾病/人群相关的心理社会需求的现有证据,可以促进临床实践的实际改变,从而借助专科/疾病/人群相关指导,帮助临床医生进一步定制并推动该模型及所提出方法的实际实施。例如,在青少年医学领域:
- 一方面,史密斯等人将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与基于证据的以患者为中心的访谈方法相结合,这一关键进展解决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三大主要问题,并推动了该模型在每次问诊中应用的操作化。
-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但已得到充分证实的证据表明,在每次问诊中都应关注青少年特定的健康和心理社会需求。这些需求在已审阅的家庭、教育/就业、饮食、活动、药物、性、自杀意念与安全(HEEADSSS)工具中有详细说明[58–60],该心理社会访谈工具被认为是获取年轻人符合发育阶段的心理社会史的金标准[61]。
借鉴史密斯等人[9]的方法学进展,通过进一步调整所提出的以患者为中心的访谈方法的描述,并参考针对特定专业/疾病/人群的心理社会需求的基于证据的建议和指导,可促进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实际实施。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政策框架和临床指南也有潜力通过多种方式推动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在实际实施中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将健康与疾病的心理社会方面纳入临床治理以及医疗质量的评估中,或重新定义并设计新角色以进一步巩固多学科和跨学科工作在常规临床实践中的地位。同样,建立一个应用健康研究议程,回应健康与疾病的身心社会理解所具有的多学科性和复杂性,可以为整合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概念和方法论层面)以及进一步完善和重塑提供依据,从而成功地将生物医学与健康及疾患的心理社会理解整合到医疗工作中。




















 289
289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