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疏水表面在血液接触型医疗器械中的应用潜力
1. 引言
具有超疏水性能的材料自发现以来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超疏水表面已被广泛研究,并应用于各个领域。由于其不润湿行为,超疏水性能在医用医疗器械用生物材料的开发中备受重视。血液接触型医疗器械在医疗环境中的诊断目的或治疗目的应用中十分常见。医用植入物和体外医疗器械,包括支架、血管移植物、心脏瓣膜、人工肾、起搏器、导丝、体外循环设备、管路和导管等,都是在应用过程中与血液密切接触的医疗器械示例。尽管这些器械在临床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血液接触型医疗器械常伴随血栓并发症[1,2]。此外,溶血和器械相关感染也常常是血液接触型医疗器械的主要缺点[3–5]。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人们已经采取了许多方法。然而,血液相容性仍然是开发用于血液接触型医疗器械的生物材料时长期存在的挑战。由于血细胞和微生物在表面的粘附机制复杂且受多种因素影响,适用于医疗器械的优质血液相容性生物材料难以制备[6]。边界条件也参与影响分子与表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超疏水表面在提高医疗器械血液相容性方面表现出良好的前景。超疏水表面上的分层结构已被证实可通过降低粘附力来提供优良的血液相容性。血液在超疏水表面边界层以更高的速度流动,从而减少血细胞与表面的碰撞频率[7]。因此,导致血细胞的粘附和变形减少。在本综述中,我们将讨论超疏水表面在缓解血液接触型医疗器械现有问题中的作用。
2. 超疏水表面的特性
超疏水表面是指表观接触角大于 150◦、接触角滞后小于 10◦、滑动角小于 10◦[6,8]的表面。接触角是水滴与固体表面接触时在接触线处形成的角度,通常用作衡量润湿性的指标。接触角滞后是前进接触角与后退接触角之间的差值,用于评估固体表面对水滴的排斥性。前进接触角通常大于后退接触角。这两个角度之间的差值越小,液滴在表面上的不粘性就越强。换句话说,具有高表观接触角和低接触角滞后的超疏水表面能使水滴轻易滚落[9]。另一方面,如果高表观接触角伴随着高接触角滞后,则称为玫瑰花瓣效应,此时液滴被钉扎在表面上[10–13]。本节将进一步讨论这两种超疏水润湿状态之间的差异。
超疏水性由两个物理原理阐明:低表面能和高表面粗糙度。表面化学组成和表面形貌是影响液体与固体界面相互作用的主要因素。表面能影响物质(包括流体和微生物)在表面上的粘附。低表面能降低黏附功,从而增强防水性。根据温德尔模型和Cassie‐Baxter模型,表面粗糙度在润湿性中起着关键作用(图1)。表面的微/纳米结构能够在其接触液体下方截留空气层,从而减少液体与固体表面之间的接触面积[9,13,14]。此外,表面气穴的存在降低了摩擦阻力,有利于流体的有效流动[15]。因此,含氟聚合物的表面粗糙度与低表面能的协同作用在超疏水性中尤为重要。
由于纳米/微米级粗糙表面和/或化学异质表面的形貌无法通过常规光学手段观察,因此这些表面的润湿性通常以表观接触角[16,17]来表征。然而,在自然界中纯的Wenzel和卡西‐巴克斯特润湿状态很少被观察到。相反,更常见的是混合润湿状态,即液滴由截留空气以及粗糙且化学均一的表面共同支撑[18]。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粗糙表面上,卡西状态也是亚稳态。截留空气可能逸出,导致转变为Wenzel状态。
为了保持Cassie状态的热力学稳定性,被截留在水滴下方的空气的临界角必须较小[19]。必须实现液/固/气系统的热力学平衡,才能形成理想润湿表面。如前所述,在Cassie‐Baxter状态中发生的截留空气现象被发现是亚稳态的,因为它会逐渐转变为Wenzel状态[16,20,21]。因此,维持气穴的截留对于Cassie状态至关重要,因为不可逆转变可能是由于水滴的凝结或蒸发等侵入行为,或通过外部压力引起的[21]。当结构化表面之间的空气间隙被水填充时,超疏水表面会失去其防水性能。Cassie‐Baxter状态表现出弱液滴粘附和降低的摩擦性能,因此提供“荷叶效应”或自清洁性能。值得注意的是,从Cassie‐Baxter状态转变为Wenzel状态会通过改变流速影响减阻效果[15]。此外,当润湿状态从Cassie‐Baxter转变为Wenzel状态时,表面会失去其自清洁效应,并反而促进水滴的粘附[21,22]。Wenzel状态使水滴钉扎在表面上(即所谓的玫瑰花瓣效应),并且表现出比卡西状态更高的接触角滞后,而卡西状态则表现出较低的接触角滞后[20]。由于表面纹理底部被完全润湿,Wenzel状态促进了液滴在表面的钉扎[21,22]。基于这两种润湿状态之间的差异,在医疗器械用超疏水表面的研发和制造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并采用Cassie‐Baxter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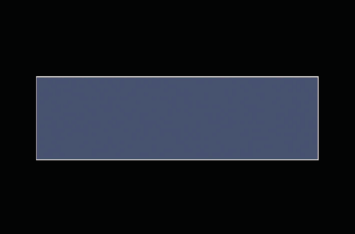
3. 超疏水表面的发展
超疏水表面的原理受到自然的启发(表1)。最经典的例子是荷叶。除了具有高接触角外,荷叶上的分层结构赋予其超疏水性。“荷叶效应”这一术语源于其自清洁行为。非黏附性的荷叶表面能够排斥水滴,并使其轻易滑落。自然界中其他超疏水表面的例子可在其他研究中找到[23,24]。虽然通过模仿荷叶来制备超疏水表面是以往研究中最常见的方法,但人体血管内壁的内皮细胞也是一种仿生结构超疏水表面[25]。
| 表1. 自然界中存在的超疏水表面示例 | ||
|---|---|---|
| 植物 | 接触角 (◦) | 参考文献 |
| 荷叶 (Nelumbo nucifera) | 162 | [24] |
| 稻叶 (Oryza sativa) | 157 | [26] |
| 中国西瓜 | 159 | [26] |
| 海滨冰草 (Leymus arenarius) | 161 | [27] |
| 穿叶蓼 (Polygonum perroliatum) | 162 | [26] |
| 苎麻叶 (Boehmeria nivea) | 164 | [26] |
| 芋头植物叶子(Colocasia esculenta) | 164 | [27] |
| 紫花假虎刺(Setcreasea purpurea) | 167 | [26] |
| 昆虫 | ||
| 马蝇(Tabanus chrysurus)翅膀 | 156 | [26] |
| 蝴蝶(Parantica sita)翅膀 | 161 | [28] |
| 沃克蝉(Meimuna opalifera)翅膀 | 165 | [26] |
| 水黾的腿 | 167.6 | [29] |
人工超疏水表面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技术制备,包括表面处理、改变其表面组成或改变其表面纹理(表2)。一些迄今为止疏水性较弱的材料可通过改性转化为超疏水材料。例如,亲水性聚乙烯醇(PVA)薄膜(接触角72.1◦)通过添加PVA纳米纤维被转化为超疏水薄膜(接触角171.2◦)[30]。在氢终止硅表面添加硅纳米纤维可使其接触角从74◦提高到160◦[31]。在光滑聚碳酸酯氨酯薄膜上引入纳米结构和氟化烷基侧链,可使其接触角从109.1◦提高至163.6◦[32]。近年来关于高效超疏水表面开发的进展已被综述,不同类型的制备超疏水表面的方法也已得到分析[9,13,33,34]。
| 表2. 人工超疏水表面的示例 | |||
|---|---|---|---|
| 材料 | 制备工艺 | 接触角 (◦) | 参考文献 |
| 碳纳米纤维 | 涂层 将碳纳米纤维与聚四氟乙烯混合形成复合分散液 | 162.1 | [35] |
| 含氟聚合物 泡沫 (氟孔) | 光引发自由基聚合 氟化全氟聚醚的甲基丙烯酸酯和醇类衍生物 | 163.7 | [36] |
| 石墨烯 | 还原氧化石墨烯 硅烷表面处理 | 157 | [37] |
| 聚苯乙烯薄膜 | 在多孔模板上真空浇铸聚苯乙烯薄膜 多孔模板 | 151 | [38] |
| 静电纺丝聚苯乙烯薄膜 并用…改性 | 全氟癸基三氯硅烷蒸气沉积 | 168 | [39] |
| 聚四氟乙烯 | 使用氩气的等离子体刻蚀处理 和氧气 | 171.4 | [40] |
| 二氧化硅 | 二氧化硅纳米颗粒的混合 与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混合以形成分散液 | 163.3 | [41] |
| 钛 | 阳极氧化过程并进行改性 通过化学气相沉积法进行 (十七氟‐1,1,2,2‐三氯(四氢癸基)硅烷 | 164 | [42] |
如前所述,表面形貌可能是在影响超疏水性方面的关键因素。表面粗糙度赋予更高的表观接触角,从而增强表面的润湿性。正如Cassie和Baxter所描述的,该表面表面纹理在突起之间形成气穴。这些气穴限制了液体与固体表面的接触点。改变表面纹理是增强超疏水性能的一种简单且经济的方法。借助现代技术,可以通过氧气等离子体处理或通过一种称为纳米压印工艺的简单光刻技术,在表面制造纳米结构,从而增加表面粗糙度[43]。另一方面,改变表面化学组成是制备超疏水表面的另一种方法[44]。
构成分级图案化表面的突起高度是影响表面自清洁能力的一个因素。当突起足够高,使得污染物部分填充在其间,或污染物足够小而能够渗透进入涂层时,会导致表面滚动角增大,从而使自清洁效应失效。孔径小于500 nm的微/纳米图案化表面可抵御大多数类型的颗粒污染[45]。另一方面,另一项研究表明,突起尺寸范围小于5 µm的微结构表面可通过雾轻松清洗,因为雾中水滴的尺寸似乎大于[46]。
通过在表面引入具有适当高度和宽度的结构,可以增强自清洁性能。突起高度较低且突起尺寸较宽时,污染物附着的接触面积更大,导致更难去除。当突起间距足够大,可防止污染物填充其间隙,同时突起将水滴抬高,赋予其低滚动角,此时认为自清洁效应是可行的[46]。
通过改变表面结构同时保持目标表面的化学成分,可以增强超疏水性能,正如毛等人和柳等人所报道的[38,40]。这两项研究均将光滑聚合物表面转化为理想的血液接触型超疏水生物材料。毛等人通过模仿荷叶的结构制备了聚苯乙烯纳米管薄膜,而柳等人则对聚四氟乙烯进行了等离子体刻蚀。这些超疏水聚合物表面表现出高的接触角,分别为151◦和171.4◦。除了自清洁效应外,该表面还表现出高耐久性,尽管在长期使用并暴露于空气后,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纳米级结构表面存在可忽略的变形。重要的是,超疏水薄膜的纳米/微米结构有助于降低血细胞和血小板的黏附。另一方面,赫尔默等人通过简单的一步光引发自由基聚合制备了一种透明的氟化聚合物泡沫[36]。这种泡沫状聚合物的纳米/微米结构赋予其超疏水特性,接触角为163.7◦,接触角滞后为6.1◦。这种易于制备的材料也具有耐磨性。分级表面粗糙度被证实能够增强超疏水效应,从而改善抗凝血和拒血效果。
4. 超疏水表面对医疗器械的潜在作用
4.1. 超疏水表面的抗溶血效应
与牛顿流体水不同,血液是一种剪切稀化流体。剪切应力会导致红细胞破裂或发生形态改变,从而因红细胞浓度降低而使血液黏度下降,这一现象赋予了血液非牛顿行为。器械相关溶血是血液接触型医疗器械中遇到的严重并发症之一。溶血会导致血红蛋白(Hb)和二磷酸腺苷(ADP)释放,进而刺激血小板活化。释放的Hb会抑制一氧化氮以抑制血小板活化[47]。这一系列反应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血栓事件。在芯片实验室应用中,选择性差也可能由器械相关溶血所致。
器械相关溶血的机制指的是由血流中的剪切力或血细胞与表面之间的物理接触所导致的损伤。作用在血细胞上的剪切应力强度取决于其位置、细胞在剪切场中的变形和方向,以及血液中其他细胞和组分的接近程度。如果施加较大的剪切力,可能会导致红细胞膜结构发生不可逆的变形。血液‐表面相互作用也应作为溶血因素予以考虑[48]。
与血液流速为零的无滑移边界相比,超疏水表面通过形成有效的滑移边界减少阻力,从而润滑流体流动。减阻的原因在于固液界面间稳定的空气层减少了表面摩擦力。随着表面摩擦力降低,血液流动在最小剪切应力[49]下因滑移速度加快而得到增强。该推论与霍希安等人[6]的研究结果一致。由于水力阻力降低,血液流经超疏水表面时所受的剪切力和黏性阻力显著减小。超疏水表面表现出优异的抗血液粘附性能,能够实现无宏观损耗的血液输送。血滴可从超疏水表面滑落,通过轻柔冲洗即可完全去除,无任何残留物。
另一方面,欧阳等人提出,疏水表面捕获的空气层减少了液体与固体表面之间的接触面积。因此,这导致流体流经近超疏水/超疏水表面时所受到的剪切应力降低[50]。当血液流经涂有近超疏水表面的聚氯乙烯管时,观察到溶血率降低。尽管存在无滑移边界条件[51],该近超疏水表面仍使红细胞在流体‐固体界面流动时所受剪切应力减小。
红细胞在接触医疗器械表面时会吸附于表面,进而导致血细胞聚集。因此,即使在渗透条件下,红细胞也容易发生溶血(图2)。有报道称,低表面自由能可减少血细胞与表面之间的碰撞,而多尺度结构化表面可减小血细胞与表面之间的接触面积[7,52,53]。因此,细胞‐表面相互作用引起的红细胞变性的概率将降低。

4.2. 超疏水表面的抗血栓作用
医疗器械诱导的血栓形成是一个必须随时应对的主要问题。血浆蛋白在表面的吸附一旦接触血液就会发生与医疗器械发生物理接触。随后,将发生一系列机制,最终导致血液凝固[33,47]。这些血小板促进邻近血小板的活化,并进一步导致血小板的黏附和聚集。最终,这些聚集体由纤维蛋白稳定形成血栓。血液凝固级联反应可通过内源性途径以及外源性途径被激活。两条途径均会导致血栓形成。这些血栓并发症常出现在体外循环回路、血管移植物、中心静脉导管、机械心脏瓣膜、留置装置和植入物上,因为医疗器械中的凝血机制是通过内源性途径介导的[1]。
迄今为止,已研究了多种方法以减轻因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和血小板在医疗器械表面粘附而导致的凝血问题。对于使用医疗器械的患者,通常联合使用全身性抗凝剂和/或抗血小板药物以减少血栓形成[54,55]。然而,抗凝剂给药需要进行适当监测,以预防出血并发症,确保患者安全。此外,先前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抗凝剂都适用于留置装置患者,因为它们未能提供有益的效果[56]。另一方面,将肝素固定于血液接触表面已被证实可减少血栓形成,同时降低抗凝剂使用量[3,57,58]。除了抗血栓作用外,与未处理表面相比,结合肝素的表面通过表现出类似荷叶的微结构而具有增强的疏水性[59]。然而,肝素涂层材料可能会引起渗漏问题,导致抗凝效果随时间减弱[3,57]。如上所述,这些策略各自存在局限性和缺点。因此,超疏水生物材料被认为是一种有望减少医疗器械血栓形成的策略。
纤维蛋白原是首个吸附在接触表面的血浆蛋白[1]。因此,限制纤维蛋白原的附着可能减轻后续血栓形成的并发症。通过改性钛表面形成纳米结构化且低表面能的表面,可显著降低纤维蛋白原从富血小板血浆中的吸附[60]。气穴的存在使得血液与纳米结构化超疏水表面之间的接触最小化。此外,超疏水表面赋予滑移边界,有助于血流顺畅流动而不促进细胞‐表面相互作用[49]。超疏水表面倾向于排斥血细胞,避免其直接接触,从而减少因细胞‐表面相互作用导致的物理损伤。该机制限制了细胞分子和蛋白质附着于表面,进而降低血栓事件的发生概率。
超疏水表面的抗黏附特性已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例如,通过仿生天然血管内皮表面的多尺度微/纳米结构,已开发出超疏水表面。这种抗粘附特性归因于超疏水表面的分级纳米结构,其为血小板锚定提供了更小的接触点[61]。Koc 等人此前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纳米结构氟化表面的疏水性增强以及可用于蛋白质吸附的界面面积减少,从而表现出对蛋白质粘附的抵抗能力。超疏水表面并非完全抑制细胞粘附,而是促进解吸和脱离[62]。与 Lim 等人的研究一致,血液与表面之间的有效接触面积减少往往会抑制血液凝固[33]。
结构化表面通常因突起而变得粗糙,且突起的高度与剪切应力相关。在血流条件下,突起顶部的剪切应力高于基底区域的剪切应力。这种剪切应力差异通过减少血小板从上部区域向底部区域的转移,从而抑制血小板粘附。因此,基底区域的血小板粘附较少,而在突起顶端则发生血流诱导的血小板解吸。除了突起高度外,突起之间的间距区域也被报道为关键因素影响血小板粘附的因素(图3)。当凸起之间的间距减小时,剪切应力差异降低[63]。相反,表面的极端粗糙度(<50 nm)对血小板粘附影响较小。由于表面特征小于血小板伪足的尺寸,该表面对于粗糙度的影响而言足够光滑,可忽略不计[64]。

总之,超疏水表面被证实比未经处理的光滑表面具有更低的血栓形成性。此外,与通过肝素或其他抗凝剂固定进行表面改性的方法相比,超疏水表面似乎是一种很有前景的减少血栓形成的方法。超疏水表面减少了血小板和血细胞的融合,从而阻碍了血栓的形成。超疏水表面的血液排斥特性显著降低了血液凝固的倾向。鉴于这些特性,超疏水表面为长期存在的与血液相关的生物医学设备和血管植入物的血栓形成性问题提供了潜在的解决方案。
4.3. 超疏水表面的抗菌和防污性能
器械相关感染,例如导管相关血流感染,一直是住院患者中的主要健康风险,特别是那些使用植入性医疗器械的患者。当医疗器械暴露于血液中时,血流中的微生物便有机会粘附到表面。最初附着在表面的细菌开始形成微菌落。这些微菌落随后分化为结构致密的生物膜,对抗菌剂具有高度耐受性。生物膜主要由蛋白质和多糖组成,为细菌群落提供保护屏障,使其免受极端环境和多种抗生素的影响[65–68]。
目前正在研究多种方法以降低由此并发症导致的死亡率,包括杀菌剂涂层、表面释放抗生素以及促进非致病性细菌黏附的材料。然而,这些方法尚未被证实能有效解决相关问题[42,69]例如,抗菌材料通过释放杀菌剂来杀灭医疗器械表面存在的微生物,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然而,当抗感染化合物浓度下降并低于致死浓度时,其杀菌活性将逐渐减弱,反而可能带来风险。亚致死剂量的抗生素使用已被证明会加速耐药途径和生物膜形成[58]此外,在医疗器械中引入杀菌剂可能导致细菌耐药性并引发毒性[69]另一方面,最近有报道称超疏水表面或材料可作为一种潜在策略。超疏水表面表现出“荷叶效应”,其抗生物污染性能可减少蛋白质吸附[8,70]由于粘附力较低,流体在通过超疏水表面时不会留下痕迹,同时倾向于带走沿途的物质。
粗糙形貌减少了微生物与超疏水表面之间的接触面积,从而降低了生物污染的可能性。具有适当高度和间距的突起结构能够在表面结构中截留足够的空气。这些截留的空气有助于实现较低的滑动角,从而实现自清洁。固液界面间较高的截留空气比例显著增强了防污性能[18]。突起所形成的局部曲率减少了细菌细胞的锚定位点。另一方面,当结构化表面之间的间距小于细菌细胞尺寸时,很可能有效阻止细菌的附着[71]。
此外,已有研究报道了表面能与细菌黏附之间的相关性。表面自由能在约25 mN/m时,可能降低细菌的存活率[72]。据报道,氟化涂层可通过将表面自由能调节至约20–30 mN/m,有效防止污染[73]。另一项关于氟化多孔表面的研究表明,相较于细菌在光滑表面上的随机分布黏附,其细菌黏附较少。氟化通过降低表面能改变了黏附功,从而促进自清洁效应。细菌黏附被认为与表面粗糙结构及宏观/微观图案的空间分布相关[39]。
詹金斯等人最近报道了纳米结构材料的杀菌效果。这些纳米结构表面通过机械破裂细菌细胞表现出抗菌活性。研究表明,表面改性增强了二氧化钛表面的光催化抗菌活性。然而,在钛表面上进一步构建纳米柱结构可诱导细菌包膜变形和细菌穿透。纳米柱表面结构通过增加活性氧引发细菌内的氧化应激反应,从而导致细菌包膜形态变形[74]。弗兰科利尼等人的另一项相关研究也证实了二氧化钛通过光生活性氧引起的氧化应激实现其抗菌活性[75]。
巴特利特等人通过阳极氧化和(十七氟‐1,1,2,2‐四氢癸基)三氯硅烷的化学气相沉积法[42]制备了一种超疏水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该二氧化钛表面表现出超疏水特性,其接触角、接触角滞后和滚动角分别为 164◦、3◦和 3◦。在荧光显微镜观察下,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在二氧化钛表面的粘附量较少,且无生物膜形成。然而,应注意的是,该表面的超疏水性并不能完全排斥细菌。相反,细菌会粘附在纳米管阵列的沟槽和/或间隙中。
克里克等人报道,通过气溶胶辅助化学气相沉积法从硅酮弹性体制造的超疏水表面显著减少了Escherichia coli(E. coli)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76]的数量。此外,佩尔尼特斯等人将聚苯乙烯颗粒沉积在表面,并通过导电聚噻吩的电聚合进一步修饰该表面。该超疏水表面表现出对革兰氏阴性E. coli结合[77]的抗性。
如前所述,表面自由能和表面粗糙度在抑制细菌黏附方面需要被考虑。当与图案化表面接触时,细菌细胞膜会悬挂在微/纳米结构的间距之间。这种拉伸最终会导致膜破裂。具有高高宽比的纳米纹理表面表现出更高的细胞黏附强度。以往大多数研究表明,超疏水表面对革兰氏阴性菌的附着抵抗能力优于对革兰氏阳性菌的抵抗能力。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革兰氏阴性菌与革兰氏阳性菌细胞之间的结构差异所致。革兰氏阳性菌的细胞壁由厚且多层的肽聚糖结构组成,因此相较于革兰氏阴性菌,革兰氏阳性菌对物理破坏具有更强的抵抗力[78]。有趣的是,革兰氏阳性菌细胞,包括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和 Staphylococcus aureus,更常出现在与植入性医疗器械相关的感染中,因为它们是人类皮肤和黏膜上最常见的共生细菌(见表3)[79]。然而,与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在粗糙表面上的黏附和生长更强,而 Staphylococcus aureus则更倾向于在光滑表面上附着[80,81]。鉴于此,不同细菌细胞在超疏水表面上的相互作用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以改善超疏水表面针对不同细菌细胞的抗菌功能。
| 表3. 医疗器械相关感染示例及其常见致病菌 | ||
|---|---|---|
| 医疗器械相关感染类型 | 致病微生物 | |
| 中心静脉导管感染 | 革兰氏阳性菌 | 表皮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革兰氏阴性菌 | 铜绿假单胞菌 肺炎克雷伯菌 粪肠球菌 | |
| 机械性心脏瓣膜感染 | 革兰氏阳性菌 | 表皮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链球菌 spp. |
| 其他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 | 革兰氏阳性菌 | 表皮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链球菌 spp. |
| 革兰氏阴性菌 | 假单胞菌 spp. Enterococcus spp. |
5. 医疗器械的近期超疏水改性
Bark Jr. 等人通过在医疗器械上喷涂超疏水分级涂层,对机械心脏瓣膜进行了改性。据报道,该微/纳米级分级结构通过增强疏水性而表现出极低的滚动角,因而能够排斥血液。经改性的机械心脏瓣膜表面可在表面形成流体滑移,从而改变血流动力学性能。它可最大限度地减少血细胞粘附,同时不损伤血液。报告指出,超疏水表面通过减阻降低了剪切应力,从而减少了装置中的能量耗散[3]。
类似地,Tan 等人通过引入一种儿茶酚胺——聚去甲肾上腺素[84],进一步完善了心血管器械的表面改性。这种聚去甲肾上腺素涂层被制备为一种克服支架和移植物等心血管器械中血栓并发症的策略。这种多功能涂层表现出对血小板细胞的低粘附性和低激活性,从而显示出抗血栓效果。此外,由于儿茶酚胺涂层对血管细胞具有选择性,有助于促进内皮细胞的增殖,从而加速血管细胞的再生。尽管表观接触角较低,该涂层仍表现出低溶血率(<1.5%)。然而,这种儿茶酚胺涂层的血液相容性仍有待深入研究。
李及其同事通过使用固定化碳纳米纤维(CNF)设计了一种止血纱布[35]。CNF涂层分别通过将碳纳米纤维与聚四氟乙烯(PTFE)粉末和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混合制备而成。CNF/PTFE和CNF/PDMS复合材料被喷涂在棉织纱布上。CNF/PTFE涂层表面和CNF/PDMS涂层表面的血液接触角分别为153.6◦和151.4◦。该超疏水表面能够承受较大的血压,从而防止失血。此外,超疏水CNF涂层纱布表现出较低的细菌黏附性,这归因于其低表面能和粗糙结构。有趣的是,据报道这种超疏水纱布还能通过促进纤维蛋白纤维生成来加速血液凝固。形成的血凝块最终会自行轻易脱落。这种自清洁效应可通过卡西‐巴克斯特状态解释,表明在血液‐基底界面存在气穴。这些特性展示了碳纳米纤维作为止血材料的有效性。
器械相关感染由于生物膜的顽固性,一直是医疗环境中长期面临的挑战。生物膜的形成促进了致病菌向器械其他部位的扩散。细菌细胞向宿主体内传播可能导致慢性感染及进一步的并发症。鉴于此,医疗器械特别是持续与患者血液接触的侵入性器械,需要格外关注以阻止生物膜的形成。莱斯利等人将锚定液态全氟碳(TLP)涂覆在管路和导管上[57]。TLP涂层利用液态全氟碳使表面粗糙化。所形成的表面表现出超疏水性能,滑动角小于3◦。医用级全氟碳涂层表面可抵抗纤维蛋白和血小板的粘附。此外,TLP涂层在血流条件下抑制血块形成并减少血栓形成。除了抗血液黏附效应外,该涂层还能抑制生物膜的形成。
与TLP涂层管路和导管相对应,Ohko 等人通过在硅胶导管和医用管上涂覆二氧化钛(TiO2)制备了自清洁硅胶导管和医用管[85]。TiO2涂层的硅胶导管表现出显著的抗菌性能,特别是对革兰氏阴性菌Escherichia coli(E. Coli)。此外,由于TiO2涂层具有光催化性能,可通过紫外光照实现简便的自消毒。尽管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提高涂层导管的疏水性,但其杀菌效果和自消毒特性为在医疗器械上制备血液相容性超疏水涂层提供了思路。硅烷处理被证实是一种增强疏水性的策略,不仅能够降低表面自由能,还有助于提高涂层的长期稳定性[86,87]。
近年来,金属或非金属纳米颗粒被广泛综述并应用于超疏水表面或生物材料制造中。具有天然抗菌特性的金属已与其他聚合物杂化,以协同提高医疗器械的血液相容性。最近,涂等人通过应用铜‐酚‐胺涂层[88]对医用管路进行了改性。该金属螯合涂层所表现出的显著抗凝效果,为缓解医疗器械相关血栓形成提供了一种有前景的策略。此外,这些血液相容性涂层的抗菌作用已在体内和体外研究中得到证实。此外,赵等人开发的聚氨酯‐金‐聚乙二醇(PU‐Au‐PEG)杂化复合网据报道表现出显著抗性对细菌细胞的粘附。该网片的血液相容性表面适用于疝气修复,因为其在感染性疝模型上的体内杀菌性能已得到验证。此外,该网片在产生可忽略毒性的同时,不会对红细胞造成损伤[89]。
另一方面,石墨烯作为血液接触型医疗器械上的超疏水表面或涂层,也是一种极具前景的生物材料。石墨烯是一种具有蜂窝结构的sp2杂化碳二维片层。石墨烯表面通常带正电荷,可通过降低表面自由能来提高表面疏水性[90]。耿等人通过常压化学气相沉积(APCVD)在锗表面沉积了石墨烯涂层[91]。石墨烯与新鲜血液接触后的溶血率显著较低。此外,已有研究报道石墨烯涂层具有杀菌活性,其机制可能涉及物理损伤和氧化应激[92]。还应注意,石墨烯涂层也可通过静电相互作用破坏细菌膜。然而,由于非共价相互作用的存在,在石墨烯表面观察到了血小板粘附和活化的现象[91]。另一项研究强调了石墨烯涂层在棉织物上的重要意义。除了棉织物上微米级纤维素纤维提供的初级表面粗糙度外,导电石墨烯提供了低表面自由能。再通过硅烷处理引入二级纳米级粗糙度后,其超疏水性能进一步增强[93]。人们推测石墨烯还可被用作止血材料,并具有构建其他医疗器械应用的潜力,例如凝血酶蛋白检测生物传感器。
6. 结论与未来展望
近年来,生物材料的发展十分迅速。在众多研究方向中,超疏水性能被认为是开发抗血液黏附生物材料的当前趋势。超疏水是指具有高表观接触角、低表面能和高表面粗糙度的表面。研究表明,超疏水表面在缓解血液相容性长期问题方面具有潜力,尽管仍需进一步增强其效果。超疏水表面可抑制溶血并减轻血栓形成性。此外,超疏水表面的防污性能通过减少细菌及其他有机物质的粘附,防止器械相关感染。上述超疏水表面的特性被认为有望解决血液接触型医疗器械应用中存在的现有问题。
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关注在血流存在下的血液‐表面相互作用。影响超疏水特性的因素,包括表面形貌和表面化学组成,仍需进一步研究。表面化学组成所带的电荷对不同细菌表现出不同的抗黏附效应。此外,应评估超疏水材料的协同效应,以开发出完全血液相容性的生物材料。超疏水表面的耐久性和可持续性也应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超疏水表面在长时间和持续使用后的有效性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超疏水表面的物理和机械稳定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超疏水表面的抗菌效果角度来看,生物膜形成的潜在机制仍有待发现。细菌细胞对表面的初始粘附事件对生物膜形成的厚度和数量并无显著影响。生物膜形成的概率取决于细胞间相互作用,而非初始的细胞与表面粘附量。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在血液接触型医疗器械中引入超疏水表面后,相关装置感染发生的概率及其毒力。此外,不同细菌细胞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超疏水表面,因为它们在表面的粘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讨这一问题。
重要的是,目前尚未发现理想的多功能超疏水表面或材料。已有多种方法被报道用于制备高效且高质量的超疏水表面。例如,在现代技术的辅助下,飞秒激光烧蚀和静电纺丝能够提供理想且均匀的结构化表面。通过引入疏水性和低表面能的纳米颗粒和聚合物来改性表面化学组成也显示出良好的效果。本文讨论的大多数方法都较为繁琐且复杂。其中,由于制备简便,超疏水涂层的应用在当前方法中较为常见。然而,其耐用性、可持续性和细胞毒性仍有待确认。因此,开发一种经济且易于复制的方法来制备实际理想的超疏水表面仍需进一步研究。




















 321
321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