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合性踝关节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手术部位感染:一项回顾性多中心队列研究
摘要
背景 :识别手术后手术部位感染(SSI)的危险因素对于踝关节骨折手术具有重要意义,但相关证据尚不充分。本研究旨在调查闭合性踝关节骨折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ORIF)后SSI的发病率及危险因素。
方法 :纳入2015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在3个中心因闭合性踝关节骨折接受切开复位内固定术(ORIF)的患者。通过电子病历(EMR)和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PACS)获取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信息。潜在因素包括四个方面:人口统计学、损伤相关、手术相关和生化指标。采用单变量分析,并进一步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与手术部位感染(SSI)相关的因素。
结果 :住院期间,3.7%(46/1247)的患者发生手术部位感染,其中1.12%(14/1247)为深部,2.57%(32/1247)为浅表手术部位感染。大约一半的深部手术部位感染由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引起。在对混杂因素进行调整后,较高体重指数(BMI)、外科医生级别(住院医师或主治医师)、手术时长>130分钟,延迟手术、术前总蛋白<60g/L是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的显著危险因素或预测因子。
结论 :在对患者病情进行综合评估后,由专业技能更强的外科医生立即手术可有效减少手术部位感染发生。
关键词 :手术部位感染,闭合性踝关节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回顾性,多中心
引言
踝关节骨折是急诊科或骨科最常见的损伤,约占成人骨折的7.5%,在老年人中其发生率仅次于髋部和腕部骨折[1]。随着人口老龄化,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其发病率将显著上升[2]。目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ORIF)仍是治疗踝关节骨折最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对于复杂损伤[3‐7]。大量证据表明,大多数接受手术治疗的踝关节骨折患者可获得良好结果,但若出现不良事件则会影响疗效[8, 9]。英国的一项研究[10],中,科里姆及其同事评估了710例接受ORIF治疗的踝关节骨折患者,发现浅表和深部手术部位感染均会显著影响功能结果(奥勒鲁德和莫兰德踝关节评分:60 vs 90)。此外,术后手术部位感染延长了总住院时间,甚至使医疗费用增加超过300%[11]。因此,识别与手术后踝关节骨折患者发生手术部位感染相关的危险因素,对于预防或减少此类感染的发生至关重要。
先前的研究已确定了一些相关危险因素,包括高龄、更严重的损伤类型(开放性骨折、三踝骨折、骨折脱位、Weber‐C型、更高级别的软组织损伤)、手术延迟时间、较高的体重指数、吸烟状况、糖尿病和养老院居住[5, 10, 12‐15]。然而,大多数研究为单中心设计,或仅关注特定亚组,如糖尿病患者或老年患者[15‐17], ,可能受限于样本量较小和统计效能不足。此外,部分研究仅进行单变量分析而非多变量分析[12, 13], ,导致结论不明确,其独立效应尚未得到证实。大量文献已证实开放性损伤是踝部及其他部位手术后发生手术部位感染的危险因素[13, 18], ,但针对闭合性踝关节骨折的研究非常少。
鉴于此,我们开展了这项回顾性多中心研究,旨在:首先,调查住院期间闭合性踝关节骨折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率及特征;其次,验证实验室中某些危险因素或生化指标与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相关的假设。
材料与方法
研究设计、纳入和排除标准
我们在2家三级和1家二级医院开展了此项回顾性研究。三级医院是中国最高等级的医院,医疗水平最高,其次是二级和一级医院。研究开始前,已获得这3家医院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通过查询患者的电子病历(EMR),确定了2015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接受闭合性踝关节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ORIF)的所有成年患者(>=18岁)。排除标准为:患者年龄 <18岁;开放性骨折、病理性骨折;陈旧性骨折(受伤超过>21天)以及其他踝关节骨折复位固定的治疗方法,如外固定、保守治疗、手法复位内固定和牵引等。
数据收集
两名研究人员通过PACS和EMR系统查询了患者的人口统计学、损伤和手术相关特征以及生化指标信息。患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身高和体重,以及计算得到的体重指数(kg/m²)、吸烟、饮酒情况,以及合并症(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和任何原因的既往手术)。
与年龄相关的变量包括损伤机制(低能量或高能量)、骨折类型(单踝、双踝、三踝骨折)以及是否伴有伴随性脱位。低能量损伤定义为由站立高度的简单跌倒引起的踝关节骨折,高能量损伤则包括交通事故、高处坠落和体育活动。
手术相关变量包括医院级别(二级或三级)、外科医生级别(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术前住院时间(受伤至手术时间)、麻醉类型、手术时长、术中出血量、是否术中输血、术前、术中及术后抗生素使用、术后引流以及ASA分级(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
生化指标包括术前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NEUT)、淋巴细胞(LYM)、红细胞(RBC)、血红蛋白(HGB)、总蛋白(TP)、白蛋白(ALB)、球蛋白(GLOB)和血糖水平。
手术部位感染的定义
我们采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标准定义来界定手术部位感染(SSI)[19]。根据患者电子病历(EMRs)和微生物学记录中描述的症状、体征、细菌培养结果及治疗反应,确定患者的手术部位感染状态(SSI statues)。若符合以下至少一项描述,则诊断为深部手术部位感染(deep SSI):累及深部软组织、肌肉或筋膜;持续性伤口渗液或裂开;可见脓肿或坏疽,需要进行手术清创及植入物更换或移除(图1a 和 图2)。任何出现伤口问题(红、肿、热、痛)且对抗生素治疗反应良好、但不符合深部手术部位感染诊断标准的患者,均被判定为浅表手术部位感染(浅表SSI)(图1b‐e),无论其微生物学结果如何。
统计分析
两名作者负责数据分析。所有连续变量以均值 ± sd(标准差)表示,并根据临床经验设定的截断值进一步分组。根据数据情况(正态性、方差齐性),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学生t检验分析连续变量。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分析。最后,将所有变量纳入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以确定其对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的独立效应。采用Hosmer‐Lemeshow检验评估最终模型的拟合优度,P>0.05表示结果可接受。Nagelkerke R²用于量化拟合优度,值越大表示拟合优度越好。所有检验均使用SPSS 21.0软件包(SPSS公司,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进行。
结果
骨折的整体特征
在研究期间,最初共有1316例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患者被筛选进入本研究,排除4例死亡病例和65例数据不完整的患者后,最终共分析1247例(1247处骨折)。其中男性673例,女性574例。平均年龄为44.1岁(标准差14.4;范围18‐81岁),无手术部位感染患者的平均年龄为44.0岁(标准差14.2;范围18‐73岁),手术部位感染组为47.4岁(标准差14.6;范围18‐81岁)(P=0.118)。近72.6%的患者(905/1247)由低能量损伤导致,其中单踝骨折562例(45.1%),双踝骨折447例(35.8%),三踝骨折238例(19.9%)。190例(15.2%)伴有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在受伤后中位时间4.5天进行,73.0%(910/1247)的手术在伤后一周内完成。总住院时间为平均15.8天,手术部位感染组为21.8天,非手术部位感染组为15.6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手术部位感染的特征
在住院期间(4‐109天),共发生46例手术部位感染,发病率为3.7%;其中深部手术部位感染14例(1.12%),浅表手术部位感染32例(2.57%)。所有深部手术部位感染及11例浅表手术部位感染的分泌物和拭子均进行了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如下:11例(44.0%)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9例(36.0%)为多微生物感染,4例(16.0%)为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1例(4.0%)为铜绿假单胞菌。手术部位感染最早于术后第1天诊断,最晚于术后62天诊断,中位发生时间为5.5天。
单变量分析
根据表1,我们发现两组在以下变量的分类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年龄(P=0.001)、体重指数(P=0.01)、损伤机制(P<0.001)、术前住院时间的分类形式(P=0.042)、外科医生级别(P=0.036)、骨折类型(P=0.037)、切口清洁度(P=0.034)、手术时长的分类形式(P=0.049)及连续形式(101.0±66.5 vs 120.7±68.4;P=0.030)、术前总蛋白的连续形式(68.5±6.4 vs 65.9±6.8,P=0.006)以及球蛋白的连续形式(25.6±4.4 vs 23.8±4.1,P=0.006)。发生手术部位感染的患者的总住院时间为21.8天,明显长于未发生感染患者(平均15.6天)(P<0.001)。对于其他无论是分类还是连续形式的变量,两组之间均无显著差异。这些变量包括连续形式的年龄(P=0.118)、体重指数(P=0.254)、术前住院时间(P=0.112)、术中失血量(P=0.843)、术前白细胞计数(P=0.557)、中性粒细胞(P=0.321)、淋巴细胞(P=0.391)、红细胞计数(P=0.982)、血红蛋白(P=0.297)、白蛋白(P=0.215)和血糖(P=0.812),以及分类形式的性别(P=0.723)、职业(P=0.397)、并发损伤(P=0.552)、糖尿病(P=0.254)、高血压(P=0.829)、慢性心脏病(P=0.178)、医院级别(P=0.255)、当前吸烟(P=0.455)、饮酒(P=0.304)、既往手术(P=0.446)、伴随性脱位(P=0.095)、消毒类型(P=0.901)、麻醉类型(P=0.428)、术前、术中和术后抗生素使用(P=0.455,0.076,0.854)、引流使用(P=0.980)、WBC(P=0.557)、NEUT(P=0.746)、RBC(P=0.469)、HGB(P=0.343)、TP<60 (P=0.067)、Alb(P=0.215)、GLOB>30 (P=0.831)、ASA(P=0.886)和过敏史(P=0.0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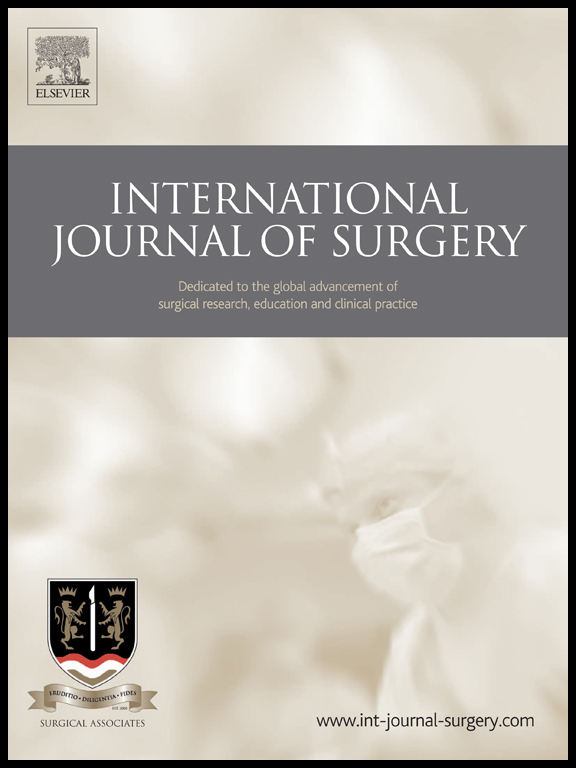

| 变量 | 非手术部位感染(均值±标准差 / n%) | 手术部位感染(平均值±标准差 / 数量 百分比) | P |
|---|---|---|---|
| Age | 44.0±14.2 | 47.4±14.6 | 0.118 |
| <50 | 746 (62.1) | 14 (30.4) | <0.001 |
| 50‐69 | 423 (35.2) | 29 (63.0) | |
| >=70 | 32 (2.7) | 3 (6.5) | |
| 性别(男性) | 647 (53.9) | 26 (3.9) | 0.723 |
| BMI | 24.6±4.14 | 25.7±4.76 | 0.254& |
| 参考文献 (<24.0) | 550 (45.8) | 13 (28.3) | 0.01 |
| 超重 (24‐27.9) | 429 (35.7) | 15 (32.6) | |
| 肥胖 (28‐31.9) | 172 (14.3) | 14 (30.4) | |
| 肥胖相关发病率 (>32) | 50 (4.2) | 4 (8.7) | |
| 职业(农民) | 828 (68.9) | 29 (63.0) | 0.397 |
| 机制(高 vs 低) 能量 | 317 (26.4) | 25 (54.3) | <0.001 |
| 术前住院时间(介于 损伤与手术) | 4.5±4.2 | 5.6±5.5 | 0.112 |
| <2d | 286 (23.8) | 12 (26.1) | 0.042 |
| 2‐6.9天 | 597 (49.7) | 15 (32.6) | |
| >=7d | 318 (26.5) | 19 (41.3) | |
| 总住院时间(天) | 15.6±11.6 | 21.8±12.5 | <0.001& |
| 并发损伤 | 0.552 | ||
| None | 994 (82.8) | 36 (78.3) | |
| 1 | 145 (12.0) | 6 (13.0) | |
| >=2 | 62 (5.2) | 4 (8.7) | |
| 糖尿病 | 79 (6.6) | 5 (10.9) | 0.254 |
| 高血压 | 144 (12.0) | 6 (13.0) | 0.829 |
| 慢性心脏病 | 36 (3.0) | 3 (6.5) | 0.178 # |
| 医院级别(级别 vs 级别) | 268(22.3) | 7 (15.2) | 0.255 |
| 外科医生级别(主治医师和 住院医师 vs 其他) | 729 (60.7) | 35 (76.1) | 0.036 |
| 当前吸烟 | 251 (20.9) | 11 (23.9) | 0.455 |
| 饮酒 | 239 (19.9) | 12 (26.1) | 0.304 |
| 任何部位的既往手术 | 294 (24.5) | 9 (19.6) | 0.446 |
| 骨折类型 | 0.037 | ||
| 单踝骨折 | 549 | 13 | |
| 双踝骨折 | 428 | 19 | |
| 三踝骨折 | 224 | 14 | |
| 伴随性脱位 | 179 (14.9) | 11 (23.9) | 0.095 |
| 切口清洁度 (- -) | 101 (8.4) | 8 (17.4) | 0.034 |
| 消毒(碘酊 与其他) | 775 (64.5) | 30 (65.2) | 0.901 |
| 麻醉类型 (区域 vs 全身) | 1145 | 45 | 0.428 |
| 手术持续时间 | 101.0±66.5 | 120.7±68.4 | 0.049 |
| =>130分钟 | 235 | 15 | 0.030 |
| 术中失血量 | 116.1±167.1 | 121.1±136.8 | 0.843 |
| 术前抗生素使用 | 186 (15.5) | 9 (19.6) | 0.455 |
| 术中抗生素使用 | 897 (74.7) | 29 (63.0) | 0.076 |
| 术后抗生素使用 | 926 (77.1) | 36 (78.3) | 0.854 |
| 引流使用 | 446 (37.1) | 17 (37.0) | 0.980 |
| 白细胞 (10⁹/L) | 7.1±2.4 | 7.3±2.5 | 0.557 |
| >10 | 199 (16.6) | 9 (19.6) | 0.593 |
| 中性粒细胞 (10⁹/L) | 5.25±2.34 | 4.98±2.49 | 0.321& |
| 中性粒细胞% (>75%) | 259 (21.6) | 9 (19.6) | 0.746 |
| 淋巴细胞 (10⁹/L) | 1.86±0.68 | 1.95±0.85 | 0.391 |
| *红细胞计数 (10¹²/L) | 4.45±0.55 | 4.45±0.60 | 0.982& |
| <下限 | 73 (6.1) | 4 (8.7) | 0.469 |
| *血红蛋白 (g/L) | 134.8±17.5 | 137.4±19.8 | 0.297& |
| <下限 | 86 (7.2) | 5 (10.9) | 0.343 |
| 总蛋白 (g/L) | 68.5±6.4 | 65.9±6.8 | 0.006& |
| 总蛋白<60g/L | 93 (7.7) | 7 (15.2) | 0.067 |
| 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 (>= 3) | 99 (8.2) | 3 (6.5) | 0.886 |
| 过敏史 | 62 (5.2) | 5 (10.9) | 0.092 |
| 白蛋白(g/L) | 42.9±4.3 | 42.1±3.9 | 0.215 |
| 白蛋白<35g/L | 59(4.9) | 4(8.7) | 0.250 |
| 球蛋白(g/L) | 25.6±4.4 | 23.8±4.1 | 0.006 |
| 球蛋白>30g/L | 197 (16.4) | 7 (15.2) | 0.831 |
| 血糖 | 5.46±1.31 | 5.26±1.10 | 0.812 |
注:*RBC,红细胞计数,参考范围:女性,3.5‐5.0/10¹²;男性,4.0‐5.5/10¹²。HGB,血红蛋白,参考范围:女性,110‐150g/L;男性,120‐160g/L;WBC,白细胞;NEUT,中性粒细胞;LYM,淋巴细胞;TP,总蛋白;ALB,白蛋白;GLOB,球蛋白;A/G,白蛋白/球蛋白;# 表示变量采用Fisher精确检验,& 表示变量采用曼‐惠特尼U检验,未标注者表示其他变量采用卡方检验或学生t检验
多变量分析
我们将所有相关变量纳入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在调整混杂因素后,较高的体重指数、外科医生级别(住院医师或主治医师)、手术时长>130分钟、延迟手术、术前总蛋白<60g/L 是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的显著危险因素或预测因子。其中,手术时长>130分钟是手术部位感染最强的危险因素,其比值比为3.16(95%置信区间,1.24‐7.62)。大致而言,体重指数每增加4个单位(kg/m²),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的风险比增加1.62倍(95%置信区间,1.06‐4.82)。结果详见表3。
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表明最终模型具有良好拟合度(X²=3.147, P值=0.531;Nagelkerke R² =0.304)。
| 变量 | Exp(B) | 95%置信区间(下限) | 95%置信区间(上限) | P |
|---|---|---|---|---|
| BMI | 1.62 | 1.06 | 4.82 | 0.032 |
| 手术时长>130分钟 | 3.16 | 1.24 | 7.62 | <0.001 |
| 外科医生级别 | 2.31 | 1.09 | 10.02 | 0.037 |
| 延迟手术 | 2.43 | 1.13 | 8.24 | 0.01 |
| 术前总蛋白<60 | 1.79 | 1.31 | 6.03 | 0.048 |
讨论
踝关节骨折术后手术部位感染(SSI)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其发病率和绝对数量呈上升趋势[2]。在本项回顾性多变量研究中,我们纳入了2家二级和1家三级医院,以验证我们的假设,即外科医生级别和某些生化指标会影响SSI的发生。本研究结果显示,闭合性踝关节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ORIF)后SSI发生率为3.7%,其中深部SSI为1.12%,浅表SSI为2.57%。
较高的体重指数、延长的手术时间(>130分钟)、延迟手术、较低的外科医生级别和较低的术前总蛋白水平(<60g/L)被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模型确定为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在所有深部手术部位感染中,44%(11例)由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36%(9例)由多重微生物引起。发生手术部位感染的患者住院时间显著长于未感染者,平均每例延长约6.2天(21.8天 vs 15.6天,P<0.001)。文献报道,深部和浅表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率分别为1.1%‐10%和2.6%‐19%[5, 10, 12, 15, 16, 20, 21]。在一项针对906例手术治疗的踝关节骨折患者的回顾性单中心研究中,纳塞尔及其同事报告浅表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为10.8%,深部手术部位感染为1.7%[18]。奥瓦斯卡等人在一项年龄和性别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中报告深部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为6.8%(131/1915)[12]。在一项印度研究中,帕特尔等人报告了最高的手术部位感染率,浅表手术部位感染为14%(7/50),深部手术部位感染为10%(5/50)[21]。本研究观察到较低的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深部为1.12%,浅表为2.57%,处于既往报道数据的下限。本研究仅纳入成年闭合性踝关节骨折患者,且手术部位感染仅在住院期间被识别,这可能解释了为何发生率较低。由于各研究在研究设计、手术部位感染定义标准以及纳入和排除标准方面存在差异,这些研究之间的比较显得困难且不切实际。未来应针对踝关节骨折的不同亚组进行荟萃分析,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较高的体重指数、延长的手术时间(>130分钟)、延迟手术、较低的外科医生级别和较低的术前总蛋白水平(<60g/L)被确定为本研究中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前三个因素在文献中已被明确证实为踝关节骨折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危险因素[12, 14, 15, 18, 22]。外科医生级别(住院医师或主治医师)是一个新发现的与SSI增加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这是迄今为止首次报道。在上述研究中,几乎所有报告术前总蛋白水平较低是SSI危险因素的研究都集中在择期手术和老年患者上。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总蛋白水平降低作为营养不良状态的重要指标,在老年人中对SSI发生的预测意义更为显著。本研究中,超过60%的踝关节骨折由进修和住院外科医生治疗,其中4.6%发生手术部位感染,是主任或副主任外科医生治疗组(2.3%)的两倍。因此,踝关节骨折,特别是严重程度较高的病例,应尽可能交由更高水平的外科医生处理。
高龄、糖尿病、当前吸烟、复杂骨折类型和伴随性脱位已被确认为踝关节骨折或其他损伤术后发生手术部位感染的显著危险因素[18,23, 24]。此外,这些因素已被证实对骨折愈合和功能恢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8, 9, 24]。然而,在本研究中,这些变量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中并未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一方面,这是由于样本量不足,导致某些变量难以达到显著性水平。例如,在本研究中,仅有6.7%的患者患有糖尿病,其中6.0%(5/84)发生了手术部位感染,是无糖尿病患者中发生率(3.52%,41/1163)的1.71倍。如果样本量进一步扩大,这种差异无疑会趋于显著。另一方面,我们推测踝关节骨折后的手术部位感染更多与软组织损伤和血供不良相关。因此,与高龄、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状况相比,医源性损伤或手术本身(如软组织剥离、骨膜剥离、组织长时间牵拉)更可能是导致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的因素[5, 25]。
本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包含了三个级别的中心、大样本量以及识别出两个先前未报道的危险因素(外科医生级别和低总蛋白水平)。本研究受限于回顾性设计和数据收集方法。单纯依赖电子病历和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可能削弱所收集数据的可靠性。由于未进行随访,患者出院后是否发生手术部位感染无法获知。因此,我们承认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被低估了。此外,骨折复位质量、内固定装置性质以及术后康复锻炼等数据未被记录,这可能影响其他潜在危险因素的识别。总之,闭合性踝关节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发生率为3.7%,其中浅表手术部位感染为2.57%,深部手术部位感染为1.12%。约一半的深部手术部位感染由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其次为多种细菌。较高的体重指数、外科医生级别(住院医师或主治医师)、手术时长>130分钟、延迟手术、术前总蛋白<60g/L是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的显著危险因素或预测因子。这些危险因素的识别对于术前预防措施的风险‐效益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因素也可作为患者及其家属咨询时的参考依据。
 踝关节骨折术后感染风险因素
踝关节骨折术后感染风险因素




















 1万+
1万+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