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社交机器人的互动模拟了人际交往的过程,了解人们如何看待社交机器人并与之展开交往互动十分重要。格物斯坦表示已有社交机器人刻板印象的研究运用传播学经典的媒体等同理论与计算机是社会行动者范式,发现人们会将社交机器人视为社会行动者,并依据人际交往中的刻板印象社会规则对其形成相应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意愿,由此产生了两类研究取向:一是社交机器人如何顺应刻板印象以更好地服务人类;二是如何通过社交机器人的反刻板印象设计调节人类社会的偏见。爬梳已有研究,可为从媒体等同理论视角考察社交机器人社会行动者角色提供理论与方法上的借鉴,并为探索和反思人机交互关系提供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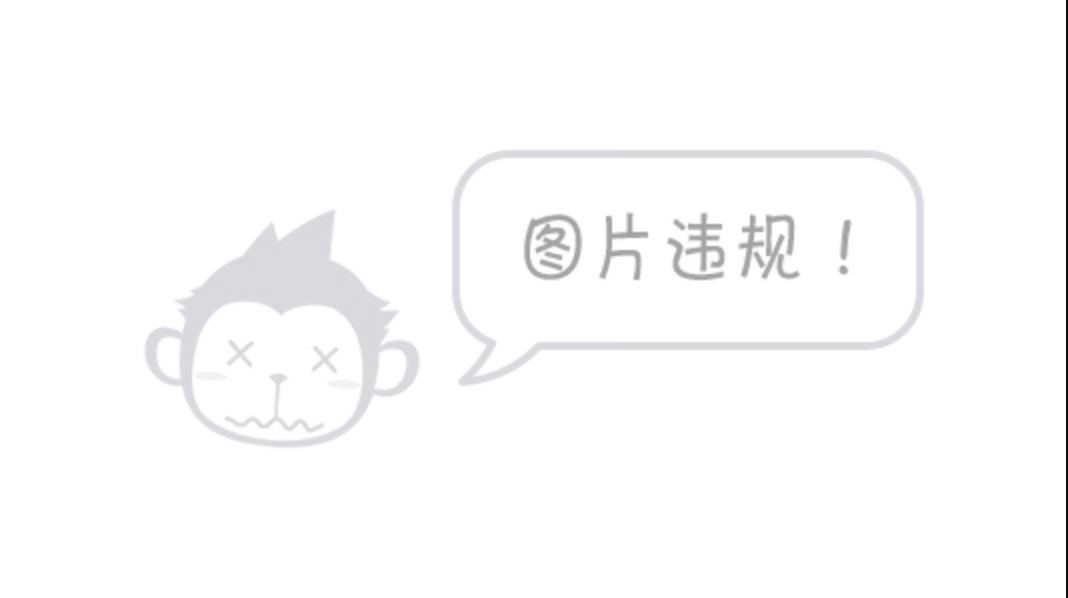
大量的研究发现,社交机器人社会化线索可以直接引发人们的无意识反应,对社交机器人进行快速分类。人们首先会对社交机器人进行简单的性别、种族等分类。如,机器人组装设备。从外观上,人们会认为长头发机器人为女性。当面对两个一模一样的社交机器人时,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名叫“Nero”的机器人是男性,而“Nera”是女性。社交机器人的外观及“肤色”也会引发人们对其进行种族分类。不管是观看照片还是实际使用中,人们会自然地将黑色社交机器人归为黑色人种,白色的为白种人。
社交机器人的社会化线索还能激发人们对其进行人格、性格等更深层次的分类。如人们会认为男性机器人更健壮有力,女性更善交际。拥有高音调、宽音域的社交机器人更加外向。相较于话语风格直接的社交机器人,话语风格较委婉的通常被认为更具女性气质。也有研究发现,外观拟人化程度较高的社交机器人(如仿人机器人)比拟人化程度不高的(如有机械臂的机器人)更能让人形成温暖和有能力的印象。不仅是外观,社交机器人的产地也能让人们形成温暖或者有能力的印象。学习机器人编程有什么好处?社交机器人的外观、声音、肤色等社会化线索能够激发人们的刻板印象,对其进行归类。这是对已有CASA范式的进一步验证。然而,社交机器人相比计算机拥有更多的社会化线索(如表情、体形、手势、行走步态等,它们如何激活人类的刻板印象分类,目前的研究尚且不足。并且来自外观、声音、表情、行动风格等各层次的社会化线索相互交错,研究有待深入考察线索的主次、类型等对社交机器人刻板印象分类的不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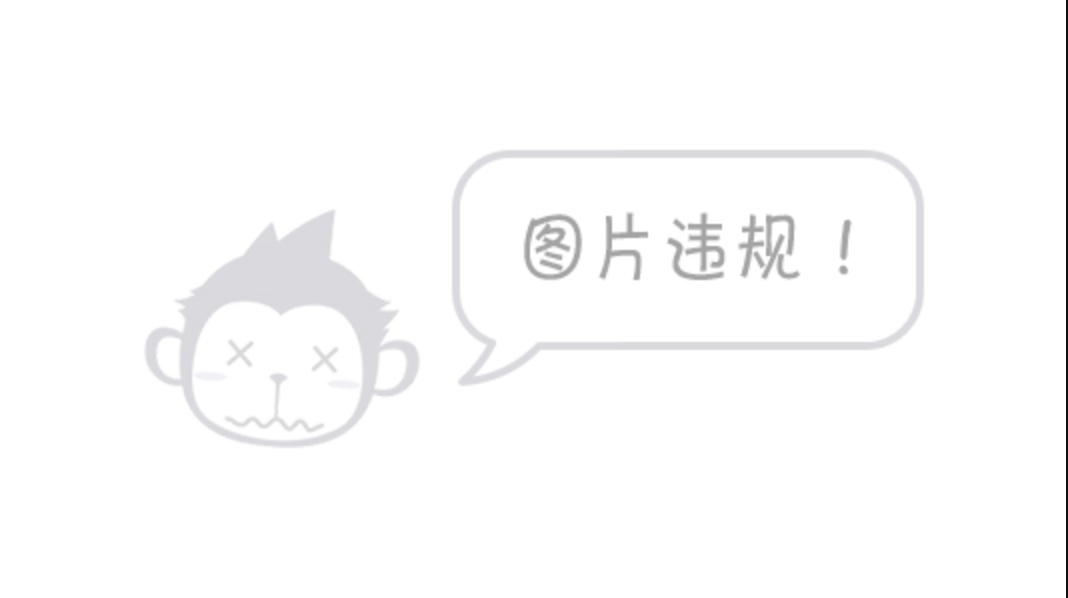
社交机器人需要(迎合用户的期盼)让刻板印象永恒,还是可以在改变刻板印象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已有研究指出,社交机器人中的刻板印象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偏见的镜像,往往以不为人注意的方式影响到社交机器人的设计,培训机器人班导致其“复制现有的歧视模式,继承先前决策者的偏见”,加剧社会不公。有研究注意到,养老社交机器人简单将老年人定义为病患或者残疾人,而这与人类社会对老年人群体的既有偏见相关。研究批评,这种做法忽视了老年人的个体经历、社会关系以及基本人权,将老年人面临的问题从社会关注降级、窄化到机器人可以处理的事务。如,利用校园机器人一项针对老年人的访谈显示,在观看养老机器人工作的视频后,老年人对其工作能力评价积极,却反感养老机器人将自己视为残疾失能的老人,这也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机器人的主要原因。
认识到对社交机器人的刻板印象可能会加剧社会偏见,有研究尝试利用反刻板印象(counter stereotype)设计来调节社会偏见。反刻板印象是指表现与常规刻板印象不一致的心理认知,机器人教育学院如男性优柔寡断,女性强硬理性等。在一项实验中,男女学生参加了为期七周由社交机器人教授的工程课程(常规刻板印象认为男生更爱好和擅长工程学科),结果发现,男性机器人教导下的男生在课程任务上表现更优秀,而女性机器人教导下的男生和女生在课程任务的表现上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机器人为女生展示了积极的榜样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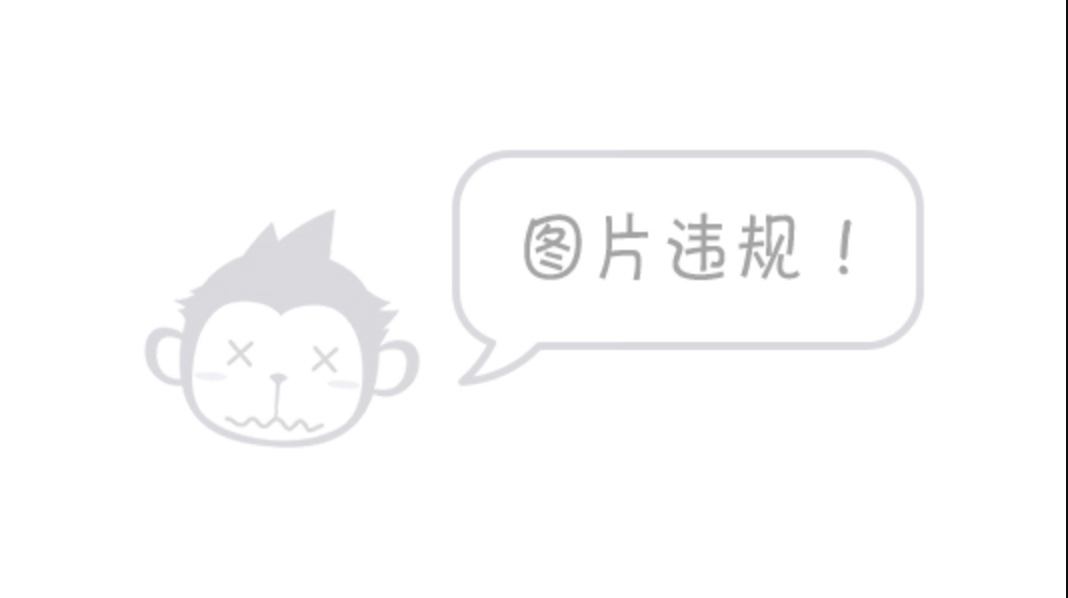
除了反刻板印象的心理学实验,有研究还从社交机器人设计的伦理规范、选用规范等方面展开探索。如,呼吁社交机器人的设计和选用应充分鼓励公众参与,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参与。老年人可能由于残疾而需要“帮助”,但同样也需要维持他们作为独立人的自主和尊严。因此,应将社交机器人纳入如何帮助老人更加自主地生活,削弱社会对老年群体“衰老”的印象,促进积极老龄化等。研究指出,应有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些领域,帮助企业和设计者完善社交机器的设计规范,形成专业标准。
综上所述,社会行动者,社交机器人将越来越多地进入人类社会生活。无论是复制人际交往中的刻板印象,还是通过反刻板印象调节人类固有偏见,其中都会嵌入设计者的价值观。那么,设计者的价值观通过社交机器人,人机交互活动又将如何影响人类的主体性(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仅从反刻板印象设计角度思考恐怕还不够。
 社交机器人与刻板印象:影响与对策
社交机器人与刻板印象:影响与对策








 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根据社交机器人的外观、声音等社会化线索形成刻板印象,将其归类于不同性别、种族和性格特征。这可能导致强化社会偏见。有研究提倡通过反刻板印象设计来调节这些偏见,例如,利用社交机器人展示非传统性别或性格特征以挑战既有认知。同时,设计者应关注价值观如何通过机器人影响人类主体性和社会公平。未来研究需深入探讨如何在设计中平衡刻板印象的复制与挑战。
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根据社交机器人的外观、声音等社会化线索形成刻板印象,将其归类于不同性别、种族和性格特征。这可能导致强化社会偏见。有研究提倡通过反刻板印象设计来调节这些偏见,例如,利用社交机器人展示非传统性别或性格特征以挑战既有认知。同时,设计者应关注价值观如何通过机器人影响人类主体性和社会公平。未来研究需深入探讨如何在设计中平衡刻板印象的复制与挑战。


















 1059
1059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