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略作重排,如有内容异常,请看原文。
原祖杰 ‖ 交流与对话:学术期刊一个被忽视的基本功能
原创 原祖杰 汇智澳门 2018 年 05 月 12 日 08:28

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中国历史学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China)联合主编
[提要]从学术期刊在 17 世纪 60 年代诞生开始,交流与对话就是其两个基本功能之一(另一个是学术成果展示)。《自然》杂志创刊初期经历了从面向公众的科学介绍到科学家内部成果交流的定位转化,体现了早期学术期刊在大众与小众之间的徘徊。学术期刊不仅应该以鼓励学术交流自任,还应该对研究型论文提出参与学术对话的规范要求。而跨学科研究的崛起,将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引向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学术期刊就应该因时制宜地鼓励和培养旨在推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学者对话的专题栏目设置。
[关键词]学术期刊 学术对话 学术争鸣 《自然》 跨学科研究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
当今世界的学术期刊据称已经具备了多方面的功能,最受推崇也是最令人敬畏的莫过于作为学术旗帜引领学术潮流,对此笔者虽不无疑虑但也不胜向往,曾经专门撰文予以讨论。按照国际通行做法,任何学术期刊都应该在其显著位置说明其宗旨与范围(aims & scope),以便让读者了解其旨趣所在。譬如被学术界公认为最早的两份学术期刊都在创刊号上说明其办刊宗旨和涉及范围,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功能就是展示学术成果和为学术交流提供平台。在这两份学术期刊创办之前,学者们靠通信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交流彼此的研究心得,重在交流。然而,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化,学术期刊的展示功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当今中国大陆的一些学术期刊,从创刊开始就将学术展示作为其主要功能,经常被定位为展示本院、本校、本区域、本国家学术成果的 “窗口”。相形之下,学术期刊作为取代学者通信的一种交流方式,其交流功能被有意无意地弱化了。这种重展示轻交流的现象不仅有违学术期刊创办的初衷,而且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经验相悖。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的话,就不能不重视交流的作用。一个封闭、孤立的文明是难以获得巨大发展和持续进步的;同样,一位学者即便是天才,也不能单靠自己的冥思苦想获得思想突破和学术发现。正因为如此,学术期刊应该发挥的作为交流平台的作用才更应该受到重视与开发,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一、早期学术交流:在大众与小众之间徘徊
1665 年 1 月 5 日法国巴黎的丹尼斯・戴萨罗(Denis de Sallo)创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学术期刊《学者杂志》(Le Journal des Savants),其主要内容为几位学者之间有关科学和学术发现的通信。同年创刊的《皇家学会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简称《哲学会刊》)也是为了给学会内外的科学家们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以取代原来靠书信往来建立的学术联系。然而,这两份最早的学术期刊从创立之初就面临着大众化与专业化之间的二难选择。与内容相对芜杂的《学者杂志》相比,由皇家学会支持的《哲学会刊》更专注于科学交流。其早期经营主要依靠作为创始人和主编的亨利・奥森伯格(Henry Oldenburg)的个人努力,皇家学会的参与更多体现于相关会员作为评审人对投稿的评估与修改。到其 1677 年去世为止,奥森伯格共主编了 136 期会刊。1752 年皇家学会全面接管了《哲学会刊》,并将其办刊宗旨调整为 “纯粹服务于学会的用途和利益”。尽管会刊在后来一个多世纪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身也逐步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但其过强的皇家学会背景却限制了学会以外科学爱好者的参与。然而,由于工业革命的作用,对科学的兴趣已经从少数精英扩大到普通知识阶层,不断增加的科学爱好者群体在 19 世纪中期催生了一批新的学术期刊,尤其是普及性的科学期刊,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自然》(Nature)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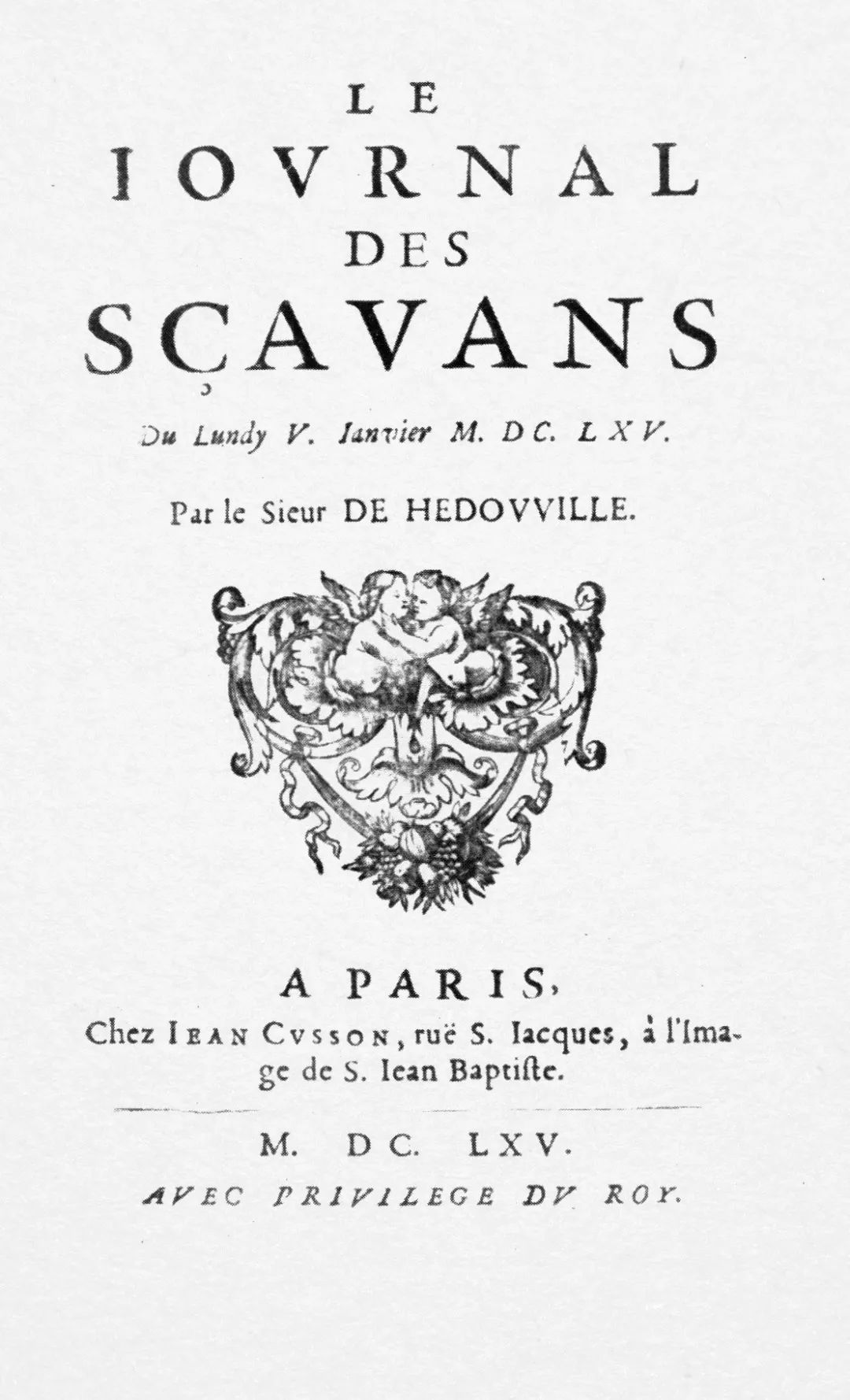
《自然》杂志的创刊人是英国天文学家、皇家天文学会会员诺尔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1862 年,居住在伦敦附近的洛克耶受其邻居、社会改革家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邀请参与了《读者》(Reader)杂志的创办,在担任该杂志科学编辑的过程中与该杂志的另一名赞助人、支持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家托马斯・H. 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相熟。几年后《读者》杂志因为经营不善被迫转手,其科学栏目也被砍掉,一直致力于科学普及的洛克耶被迫另起炉灶。1869 年 11 月 4 日,洛克耶出版了自己的杂志,命名为《自然》,蕴含着探索自然真理之意。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对科学的兴趣弥漫着整个社会,面向公众的科学杂志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洛克耶选择了对商业出版雄心勃勃的伦敦麦克米兰公司来出版自己的杂志,力图靠市场化经营来支撑这份杂志。
与《哲学会刊》等专家评审的专业型杂志不同,《自然》并不隶属或依附于任何学会或学术机构,在创立之初将自身定位为科学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其基本目标是要向普通民众介绍新的科学发现,在英国公众中培养对科学的兴趣。除此之外,洛克耶也希望能在《自然》上介绍对他和他的科学家同道们有用的信息,包括学术论文摘要、年会报告、科学讲座以及国外科学团体的研究动态等等。由于新的出版和印刷技术降低了连续出版物的出版成本,19 世纪中期的英国科学杂志成为普通中产阶级买得起的精神食粮。
洛克耶与赫胥黎担心蓬勃发展的科普介绍会误导公众,因为由科学记者撰写的科学文章很难准确地反映科学进展情况,他们认为,“掌控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的应该是科学研究者,而不是记者和兴趣爱好者。他们期望《自然》上刊登的文章能出自杰出人士之手,这些人的专业知识是基于一手的研究。这一努力的动机不只是要告知公众,而且是要将有关科学的公共信息控制在科学家手中”。作为《自然》杂志最忠实的支持者,赫胥黎一生都在致力于科学知识的教育与普及。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予不遗余力的支持,使他的形象总是与达尔文和进化论联系在一起。除了普及科学知识,推广进化论,他还努力推动科学家职业地位的建设,主张由科学家来承担科学传播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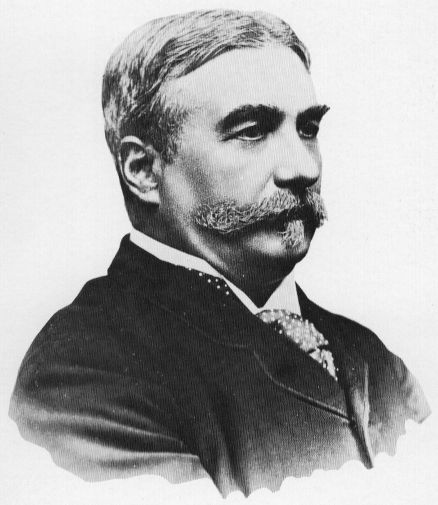
Norman Lockyer
然而,这一定位很快就遭遇到尴尬:面向公众的通俗介绍在竞争激烈的期刊市场上并没有为《自然》带来足够多的普通订户;而科学家独立办刊的前景似乎也不被看好。著名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让《自然》的出版商亚历山大・麦克米兰给洛克耶带话说:“请向洛克耶的期刊转达我的好意……(但是)名人办科学刊物的失败让人郁闷。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能够有时间科学地经营一份期刊,或者有脑力去阅读成堆的垃圾作品。” 开始几年,虽然遭遇了一定的困难,但洛克耶还是想坚持他走大众路线的初衷。他在 1870 年 1 月 20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的最后一页针对该刊的内容发表过一个简单的声明,表明该刊既要服务于大众又要照顾科学家这样的小众。针对科学家的内容 “仅限于有关摘要和会议报告方面的讨论,而将《自然》的大量版面留给能够引发‘大众’兴趣的作品”。《自然》杂志的定位问题反映了英国科学发展史上两种不同的倾向,即科学家应不应该花费大量时间撰写面向大众的作品,致力于科学普及。一种以洛克耶和赫胥黎为代表,主张走大众化道路;但多数人还是认为真正的科学家不应该把时间花在为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或者为普通人授课上,这让洛克耶向他的科学家同事们的约稿工作变得困难起来,他们更关心科学家之间围绕新发现展开的对话、分歧和争议,而对撰写面向大众的介绍性文章不感兴趣。
除了需要抉择科学家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兴趣之外,《自然》还要在学术群体内部找到自身的定位。根据梅琳达・鲍德温的研究,《自然》在创刊之初与英国当时一个叫作 X 俱乐部的顶尖科学家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个俱乐部由 9 人组成,包括赫胥黎、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与约瑟夫・胡克等一批维多利亚时代顶尖科学家。这些大牌学者主要将《自然》作为一个大众平台,用来介绍他们的科学发现或者回应对他们的质疑。《自然》为学术界很多针锋相对的争论提供平台,但结果却往往开罪某一方甚至争论双方。很多争论会有 X 俱乐部成员参与或者涉及这些成员的某些观点,令他们失望的是,洛克耶并没有将《自然》当作这个俱乐部的机关刊物,而是作为英国科学共同体的机关刊物(An Organ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in Britain)来运行的。因此,在很多观点对立的争论中,《自然》并没有偏袒 X 俱乐部成员,而是给争论双方同等的机会。这种做法让《自然》失去了 X 俱乐部的支持,除了赫胥黎继续与洛克耶保持着友谊之外,包括丁达尔、胡克、斯宾塞在内的其他知名科学家都疏远了《自然》杂志。失去这些各领域顶尖科学家的支持,对《自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损失。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自然》在学术争论中的公允立场很快赢得了一批年轻科学家的支持。与 X 俱乐部中知名科学家们只是在兴之所至时偶尔在《自然》上发表一些通俗性作品不同,年轻科学家们更愿意把《自然》当作他们阐发学术发现的园地。鲍德温评论说:“年轻一代将《自然》当作他们科学交流的中心机关(central organ),他们的投稿和热情奠定了《自然》作为英国最重要科学出版物的地位。” 疏远 X 俱乐部和赢得年轻科学家的支持促成了《自然》杂志在自我定位和刊发内容上的变化,由偏向大众注重科普,逐步转型为更为重视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
《自然》杂志的成长史为我们研究学术期刊的对话模式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对于我们认识学术与社会、学术期刊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很多启发。首先,现代学术的诞生和成长离不开一批以推动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己任并富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先驱们的共同努力,前文提到的 X 俱乐部成员及其对《自然》杂志的支持就是例证。作为该俱乐部灵魂人物的赫胥黎尤其是一位富有使命感的科学家。为了推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赫胥黎四处游说,并说服其他的科学家接受进化论观点。他在 1858 年 9 月 5 日就《物种起源》的出版问题写给既是同僚又是朋友的约瑟夫・胡克的信中说:“我期待着一场影响深远的伟大革命…… 我坚信,一个科学与艺术的英国世纪正在来临。” 在《物种起源》出版后,面对以基督教为首的传统势力的批评、攻击甚至威胁,赫胥黎一方面提醒胡克 “自我珍重”,另一方面又鼓励胡克说,“我们对于改变外部世界、对于科学应该承担起一定责任”。也正是出于对外部世界的责任感,赫胥黎和他的科学家同事们才积极推动《自然》杂志走 “大众化” 道路,面向社会,将最新科学发现通过权威科学家的文章介绍给普通社会精英(elite laymen)。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的《自然》杂志在创立之初所刊登的学术讨论尽管有很多为科学家们所执笔,针对的读者对象却不限于科学共同体,而是包括了普通社会精英。换言之,《自然》在很多有关科学问题的对话中,充当了联系科学家与普通人的公共平台。

其次,如果说在社会上取得现代科学的合法地位是科学家们的第一使命的话,那么建立职业化的科学家队伍和科学共同体,规范科学研究模式,改进学术对话的质量,则成为科学家们需要肩负的第二使命。对于科学家们做出的这两种努力我们都可以在《自然》杂志的早期发展中找到印记。19 世纪后半期,包括参考书目(bibliographical catalogues)、文摘类期刊(abstract journals)、年度报告(Jahresberichte)、术语索引(nomenclatural indexes)在内的许多新的出版形式纷纷出现,目标在于使科学研究的文字发表更规范、更有效。这些努力在英国造成的问题就是围绕《自然》杂志的定位问题出现的紧张 —— 是走大众化道路还是走专业化道路。科学共同体一旦形成并取得了合法地位,大部分科学家们便不再满足于或者不再有耐心面向社会介绍他们的科研成果,他们的学术对话更愿意在同行之间,至少是科学共同体内部展开。这或许是推动《自然》等向专业化期刊(specialized periodical)转型的主要原因。换言之,学术期刊的专业化是科学发展带动的必然趋势。
《自然》早期发展史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个启示就是学术期刊的开放性问题。《自然》杂志在竞争激烈的维多利亚英国期刊界的立足,离不开 X 俱乐部中几位顶尖科学家的支持,这对于前者来说自然也是一种十分宝贵的财富。然而,作为当时英国各学科领域领军人物的这批顶尖科学家,在支持《自然》的同时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对自己观点学说的私心和偏爱,在与其他学者产生争议时,试图将《自然》当作维护他们学说的领地。值得庆幸的是,《自然》杂志主编洛克耶宁可开罪这些学术大佬也要给予学术对话的参与者以公平的表达意见的机会,这对于维护《自然》作为公共平台的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期刊界一直在强调学术期刊的特色化建设,需要期刊人警醒的是,任何对 “特色” 的强调都会带来对不能体现其特色的作品的排斥。因此过度地强调某种特色,甚至突出某种意识形态特色,必然会破坏学术生态的平衡,扼杀学术的生命力。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公共平台,其开放性和包容性还是需要办刊人用心去把握和呵护的。
二、学术交流是研究型文章的旨趣所在
学术期刊出现以后,随着其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作为一个发表平台,其展示的功能很快超越了其交流的功能。与彼此交流相比,学者们更注重如何展示他们的学术发现。学术期刊的展示功能不断得以强化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将发表作为一种发明 “注册”,宣示知识产权的占有,本来就是学术期刊出现之初肩负的两个重要使命之一。其次,随着 18 世纪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大学等学术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科学和思想的发明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科学家本人需要发明的专利和荣誉,科学家们所在的学术机构也将学术发表视为其存在价值的证明而持之不懈地予以追求。因此,作为成果展示的学术发表,不仅成了个人学术追求的目标,而且成了岗位竞争、职务晋升乃至学院和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当然,不可否认,展示本身也是一种交流。现代社会的几乎任何发现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和探索基础之上的,对新发现的展示不能忽略对别人成果的借鉴,正因为如此,学术引证才成为学术发表的基本规范。一篇优秀的学术文章不应该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研究团队的自说自话,而应该是在充分参考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的新发现和新建树。
一份好的学术期刊是需要好的学术文章来支撑的。专家学者和学术期刊编辑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很多学者对于如何进行学术论文写作、如何写出好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任继愈在《谈学术文章写作》一文中重点强调了文章的学术性。他写道:
学术文章,先有 “学术”,再谈 “文章”,因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学术内容,而不是词藻、结构、章法。旧社会所谓 “桐城义法” 写不出学术论文,用 “马列义法” 装点的文章多短命,有的文章连一两年的寿命也没有维持下来,一点也不奇怪,理应如此,因为文章缺少科学性。

文章的学术性或科学性应该是对一篇文章的总体评价,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任先生在那篇原发于《光明日报》1986 年 12 月 1 日的随笔中并没有给出详细说明。对于这一问题,期刊界比较一致的回答是好选题、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以及严密的逻辑论证。从笔者经常收到的学术期刊外审意见书中也可以看出,各家学术期刊对论文质量的关注不外乎以上几点。例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外审意见书所列各项分别为:选题价值、学术创见、研究方法、分析论证、文献征引、语言表述和总体评价。《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效仿《中国社会科学》采用了同样的评价指标。《美国研究》的评审标准则简化为四项:创新性、逻辑性、学术规范和文献基础。另一家大学学报的评审意见书也开列了四项评价标准:创新性、学术性、规范性和可读性。而笔者联合主编的英文刊 *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前沿》)向评审人征询的问题则包括:(1)您如何评价作品的重要性?(2)文章是否包含新的或鲜为人知的材料?(3)文章是否对相关话题有新的理解?(4)文章体现的学术性(scholarship)如何(优、良、中、差)?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术期刊对于研究型文章的评价标准基本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国内学术发表广受诟病,难以走出去?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以笔者的观察,至少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国内学术文章大多重展示、轻对话,不能充分参考所选课题的已有成果,因而对学术界关注的研究难以做出有针对性的贡献,其重要性也就很容易被低估。下面将结合上述各期刊关心的一些评价标准,就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去,与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形成对话略抒管见。
首先是选题和创见问题。中国学术界对于学术文章和学术专著选题的评价经常受到现实问题的影响,除了学术价值外还要看选题的现实意义。这一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课题申报中对选题应用价值论证的影响。由于当前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中课题文章占据了多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也成了期刊的一大特色。以至于很多文章在写作风格上出现八股式的雷同:开篇即强调选题对于国家与社会的重大意义;正文却往往与开头强调的问题没有多少关系;结尾则又回到开头的现实关怀。看似形成呼应,其实却像一个身体瘦小的人头戴大帽子脚穿大鞋子,破坏了文章的整体结构。这一套路或轻或重地表现在众多学术文章中,让一些国外学者为之费解。另一方面,笔者也听到国内部分学者对于过去二三十年欧美学术影响下的中国学术研究碎片化的批评,认为造成这种碎片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下学术研究缺少对历史和现实的整体关怀。由此可见,彼此间存在着认知误差的中外学术群体很难形成顺畅的学术交流。
那么,是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没有社会关怀?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欧美历史学界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讨论的许多有关帝制晚期中国的话题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现实关怀和学术政治的影子:从对西方中心论和 “冲击 — 反应模式” 的批判、对 “资本主义萌芽” 问题的反思,到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和民间社会的讨论,再到新清史关注的清朝的治理和清代的疆域等热门话题,背后都隐含着某种政治倾向,只不过这些现实关怀或者政治考量一般不会赤裸裸地表现在论文中,不然就影响到学术的严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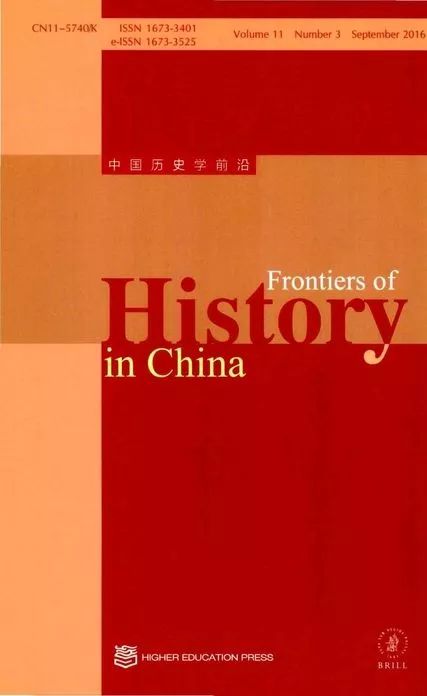
中外学术界普遍认同的选题策略是通过一个较为具体的研究回应一个大的问题,即所谓问题意识。李剑鸣在讨论历史写作时,系统阐释了选题策略中的 “以大观小”、“小题大作” 和 “因小见大”:
“以大观小”,是指用 “大历史” 的眼光来看待 “小问题”,找到 “小问题” 在大历史中的确切位置,明了 “小问题” 对理解 “大历史” 的意义。……“小题大作”,就是下最大的功夫来研究 “小问题”,用全部的学力和详尽的材料来探讨 “小问题”。……“因小见大”,意思是要将 “小问题” 与本领域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为解答这些基本问题提供知识或思路,并通过若干 “小问题” 的连缀,最终能够看出 “大历史” 的一斑。
而要做到以上三点,则需要深厚的学养积累、敏锐的学术洞察和热情的人文关怀。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即便对 “大历史” 有所领悟,却也很难创立前无古人的万世之作,更多的学术发表是通过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来切入一个较大的话题,尤其是已经在当前国际学术界成为 “时尚” 的话题。这就需要对世界范围的研究动态有及时、准确的把握,然后才能参与讨论。总之,合理的选题应该是能够通过具体研究参与正在流行的宏观讨论的问题。

其次,是分析论证和文献征引问题。一篇论证紧凑的文章,一定是围绕一个主题而展开的。这个主题就是英文写作中的 “thesis”,是整篇文章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李剑鸣指出:“一项研究总是从提出问题开始,通过回答问题而展开,最后以解决问题而告完成。无论是一篇论文,还是一部巨著,都应当有一个中心问题,否则主题就不明确。” 前文已经提到,主题的选择是建立在对相关研究的洞察和把握基础之上的。对相关问题研究现状的精确了解,是开启研究、展开论证的前提。一项课题的申报往往会要求申请人描述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这一做法也被一些学术期刊采用,要求作者在文章开头提供一个学术综述,并将之纳入必须遵守的学术规范。2000 年《历史研究》等 7 家学术期刊联合发表了《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声明中提出:“学术研究必须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凡专题研究论文,应就主要的研究内容,概略说明或介绍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或研究状况;此种说明或介绍,可以列入正文,亦可采用注释的方式;完全没有此种说明或介绍的来稿,各刊编辑部将不予受理。” 翌年《史学月刊》等期刊编辑部也纷纷效仿,作出声明:“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凡研究性论文,均应有学术史的回顾,在文中或注释中简要说明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状况。完全没有此类文字的稿件,本刊不予受理。” 一批权威性期刊将学术综述作为提交论文的前提条件,学者们即使不情愿也不得不做出让步。于是,我们就经常看到很多文章在引语部分罗列出数篇与主题相关的研究文章和专著,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式学术文章的特色。应该说,这一要求在中国的特殊学术环境下是不无道理的,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已有的研究和遗留的问题。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不能仅限于文章开头的文献罗列,而是要在论证过程中与已有的研究形成对话,甚至不限于对同一课题的研究的对话,对话的范围经常要包括论证中涉及的某些边缘性问题,尤其是著名学者对这些问题提出的重要见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欧美学者撰写的研究型文章总是旁征博引、资料丰富的缘故。一篇翔实的研究型文章(solid study),通常要罗列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参考文献。珍贵可靠的原始文献固然重要,二手文献的阅读和梳理同样能帮助作者强化问题意识,提炼学术创见。
总之,学术发表的目的除了展示作者的学术发现和见解之外,更应该注重其学术交流作用。现代学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很多学科门类都形成了较为严密的体系,每一步学术进展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即使对某一问题的初始发现和独立见解也往往是得益于前人对其他问题研究的启发。有意无意地忽视别人有价值的研究,不仅不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也是学风上的瑕疵。
三、学术交流的延伸:跨学科、跨领域对话
前文中讨论的学术对话主要涉及的是某一学科领域内部的对话。现代学科的划分始于早期近代的欧洲,19 世纪上半叶首先在德国大学中与课程设置联系在一起;20 世纪之前学科划分还是比较宽泛的,到 20 世纪才逐渐精细化。尤其是 20 世纪后半期,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虽然有助于研究深度的推进,却不利于研究视野的扩展,并桎梏了学术对话的范围,进而遏制了学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20 世纪后期欧美一些学者和学术机构在意识到这一问题之后,开始在大学中推动跨学科研究。
跨学科研究只是一个笼统的译法,对应于德语中的 Transdisziplinarität 和英语中的 Transdisciplinarity,也包括在英语中有所区别的 Interdisciplinarity。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transdisciplinarity 关注的是学科间的(between the disciplines)、跨越不同学科的(across the different disciplines)以及超越某单一学科的(beyond each individual discipline)问题。跨学科研究的崛起主要是由于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驱动,意在将不同学科的知识、方法运用于某一问题的解决。首次提出这一术语的是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他在 1970 年的一部著作中介绍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笛卡尔。他将代数与几何学这两门古老的学科结合起来而发明了解析几何。20 世纪后期以来欧美国家的跨学科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首先表现在跨学科领域的拓展和跨学科机构的建立上。从我们所熟悉的人文、社科领域就可以看到很多跨学科研究在过去 30 年的攻城略地,如带有跨学科性质的城市研究、性别角色(gender)与妇女研究、亚太研究、欧盟研究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研究等,在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设立了研究中心和研究所。有的大学还成立了专门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协调各种跨学科研究。新的跨学科机构的设立带动了相关的学术活动,从而催生出一大批跨学科研究成果,从 “百度学术” 中就可以搜索出 8 万多篇与 “cross-disciplinary studies” 相关的学术文章,仅 2012 年以后发表的就有 3 万多篇。由此可见,跨学科研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跨学科对话已经在学术界蔚然成风。
一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跨学科研究主要包括四个层面: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和文化交融。方法交叉和理论借鉴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如中国学术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形成的岭南学派等,其他如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崛起也与此有关。问题拉动则是现在学术期刊的典型做法,如一些大学学报的三农问题、边疆问题等专题研究栏目,都是循着这一思路。文化交融就是要打破学科和文化边界,相关专题如全球化问题、环境问题等,都是既要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理论,又要兼顾不同区域、国家、民族的文化特征。无论是在哪个层面所进行的跨学科研究,都意味着研究者要关注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参与本学科、本领域之外的学术对话。
跨学科研究的崛起为综合性学术期刊提供了化劣势为优势的机会,因此也吸引着带有某种程度的综合性特征的期刊编辑们的关注,并为其提供足够的发挥空间。美国《亚洲研究杂志》主编华志坚教授在就学术期刊的不同运行模式接受访谈时指出:“如果说我在给《亚洲研究杂志》盖上一个特殊的印记的话,毋宁是鼓励发表更多的试图模糊或者跨越某些边界的作品。我一直在运用一种新的风格,如‘亚洲研究热点专题’,以将更多的作品吸引到我们的版面,来质疑传统的对于大众的,甚至流行的交流形式与高度专业的交流形式的划分。我们也在试图做更多的工作,让不同领域的亚洲学学者能够互相对话。” 过去几年,中国的众多综合性期刊也在纷纷设立跨学科研究专题栏目,为不同学科学者追踪跨学科问题留出优先版面。近年来的数据化、网络化趋势为学术期刊推动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更大灵活性。通过网络专业刊建设,以大学学报为主的综合性期刊不仅部分实现了专业化转型,也为专题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创办了《三农问题研究》、《区域文化研究》、《儒学研究》等跨学科专题刊。专题刊的发行往往有很强的问题导向,在追踪某些重大研究课题上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并鼓励了不同领域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
四、余论
以上所论学术期刊的对话与交流功能,主要从学术期刊与学术文章的基本功能角度展开的。所谓基本功能,应该是每一期学术期刊和每一篇学术文章都应该具备的功能。从广义的学术对话角度来看,同样应该受到重视和鼓励的还有学术争鸣。或许是出于 “和谐” 的考虑,近年来中国学者参与的学术争鸣越来越少,至少在正规的学术媒体中鲜见针锋相对的争鸣。作为学术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争鸣对于学术进步和哲学、社会科学繁荣有着不可低估的驱动作用,应该得到所有学术期刊的积极鼓励和有意培养。
责任编辑 刘泽生
via:
-
原祖杰 ‖ 交流与对话:学术期刊一个被忽视的基本功能
https://mp.weixin.qq.com/s/KEEYn9fulIjWQPB3R_selQ -
澳門理工學報 2016 年第 2 期 交流與對話:學術期刊一個被忽視的基本功能原祖傑 201602-110-118.pdf
https://journal.ipm.edu.mo/images/journal_c/2016_2/201602-110-118.pdf- 观点||原祖杰:中国学术为何走不出去?
https://mp.weixin.qq.com/s/tsJ5tNccVeXU4Hvs5I09GA
- 观点||原祖杰:中国学术为何走不出去?





















 6472
6472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