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一位多年好友,叫沙阿姨。他们在父亲念大学时相识,到现在,每逢过年或重要日子都会聚聚,差不多有五十年的交情了。
小时候就觉得沙阿姨是个美人,个子高挑,眉眼恬淡,椅子只坐一半,腰挺的很直,看过去干净又端庄。不像母亲对我直呼其名,她从来到家里见我,都是搂住喊宝贝儿,弄得小孩子心里甜甜的。只是记忆中的她,从来都很沉静,话少,声音不大,脸上始终有一份藏不住的忧郁。很少笑,即便有,也稍纵即逝。
父亲说,那是因为她身世很苦。她父亲是国民党官员,有了孩子后不知所踪,沙阿姨是孤女,由奶奶一手带大,后来认识我父亲,以大哥相称。父亲不上课时,经常到她们家里帮忙。家里很清贫,可是收拾的十分整洁。奶奶很喜欢我父亲,去世时把唯一的孙女托付给他照顾。但是天不遂人愿,父亲后来被分配到不同的城市工作,沙阿姨留在本城的书店,相隔两地,各自都在新的生活里沉浮,父亲和母亲结了婚,而沙阿姨始终觉得自己学历不高,配不上父亲,后来嫁给一个中学体育教师何叔。
我读小学时,家里又调回了省城,两家走动的多起来,沙阿姨有时会来我家,从不吃饭,只小坐一阵便走了,她自己工资不高,却给我父亲买昂贵的羊毛围巾。父亲不喜欢戴围巾,多年都好好的保存着,待我们成人后,每次想给他买围巾,他都连连摆手不要,说你沙阿姨给我买的有,那么好还没用过呢。
母亲从未因沙阿姨对父亲有过什么说词,倒是十分欢迎她来,和我说她实在是个好女人,大方又明事理,有时也叹息她遇人不淑。何叔没文化,嗓门大,对家事不闻不问,阿姨隐忍又好强,多少难处都自己扛。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我住校后回家少,只是偶尔从父母的对话中,听到一点点沙阿姨的消息。
多年前,市里有过一起出名的非法集资携款潜逃案件,沙阿姨家几乎所有的积蓄都被卷走了,她打电话来,提醒我家千万不要参与类似事情,又焦急又伤心,也清楚的知道追回的希望太渺茫,半生节俭打了水漂。父母当下要拿钱给她救急,她坚决不要,说谁家都不易自己还过得去。父亲取了现金送到她家,仍是被一分不少的退回,包钱的报纸印子都清晰未碰。那时她家还有不少负债,何叔怨声载道,她不知是怎么咬着牙熬过来的。
再后来大约有几年都没消息,一日回家,父亲突然告诉我,沙阿姨家出事了,她最疼爱的大儿子,在二十岁生日当晚,跟朋友庆祝,喝了酒,骑着摩托,深夜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当场不治。沙阿姨通知父亲时,嗓子都哭哑了,只说了一句,大哥,我的孩子没有了,就呜咽的再讲不出什么。去家里探望,她呆滞的坐在沙发上,脸浮肿的透着光,似乎一触就破。没有呼天抢地,只是不停的流泪。何叔没有出来见我们,自从儿子走后,他开始酗酒,酒后就骂骂咧咧,砸东砸西。后来又开始养各种动物,以寄托思念,但是从不收拾。阿姨在外忙一天,回家还要清理满地的秽物,强忍伤痛,任劳任怨。
儿子走后,年复一年,阿姨从未去过陵园祭扫,说心里承受不了,都是让女儿和小儿子去。这又是怎样的岁月呢,她提前退休了,自己做了点生意,时常东奔西跑,风尘仆仆,见面时苍老了许多,但透着一股为生活强打精神的坚强。母亲去世那年,阿姨来我家,一见面就抱着我哭,说来说去只一句话,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时节已近深秋,她给我买了一套保暖内衣,浅粉色的,手肘和膝盖都有加厚层,大小正合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暖和的衣服,只在最冷的冬天才拿出来穿,穿了很多年。衣服下摆和裤子破了几个洞,补补还继续穿,后来连补都没法补了,一次洗完晾在阳台,被父亲看见,惊讶地问我这是什么衣服,怎么破成这样还在穿。我说是沙阿姨给买的,没舍得扔。父亲深深叹了口气。
阿姨在商海中打拼的时光没过多久,何叔中风瘫倒在床,她又辞掉工作,回家来服侍,一晃又是好几年,何叔从半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每日吃拉在床上,阿姨天天都要换洗床单被褥,无论酷暑严冬。她已经很老了,头发花白,一双手关节肿大,椎间盘突出,上下楼也很困难,但是该干的活没有人替她干,孤苦的她依然要扛起这个家。那段时间,阿姨不让我们去探望,说家里味道不好。偶尔能见面,她从来都是梳洗干净,一如既往的,整洁的,微微笑着,早早等在饭店门口。席间对我们嘘寒问暖,不肯多说自己的难处,没吃完就悄悄起身去买单,和她争还会生气,说我们不能看不起她。
何叔去世之后,父亲已单身多年,我曾希望他们能走到一起,两人共同的朋友也在中间撮合。可阿姨不许任何人提,说自己条件差,怕照顾不好父亲。父亲终于也未表示过什么,后来另有所娶。婚礼上,阿姨坐在主宾席,面前的盘碟始终是空的,一直背过身去悄悄擦泪,只说替大哥高兴。
男人对女人最大的爱和责任,是给她婚姻。父亲从一开始就没选择她,第二次也没有。未必不懂那情深意重,却始终只当成好友。他没有辜负长辈的遗愿,多年都关照着她,可是又有多大用处呢,她依然是独自在命运的洪流里起起落落,从天真到白发,不争,不要,吞下眼泪,做一个好人。人间最悲情,除了千里孤坟,四顾茫茫;更有,何当共剪,却话西窗。命运从不会厚爱每个人,看似再寻常不过的相守,对有的人而言,却是穷尽一生都不能实现。
最近一次见到沙阿姨,是在给父亲庆生的宴席上。她还是没什么话,默默坐在我旁边。酒敬到跟前,她落落大方,一饮而尽。给她夹菜,她就温柔的说,宝贝儿,你也吃。一脸平静,无悲无喜。
席至一半,她提前退场了,客客气气的跟每个人道别,说家里还有事。送到楼下,看她一个人,落寞的,一拐一拐往车站走。午后烈日炎炎,空洞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很想对她说些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有时觉得我是和她一样性情的人,又深深害怕自己会成为最后凄清的她。
入秋渐深,枫叶见红,一层霜打一层明艳。短暂的灿烂后,是永恒的凋零。死,不可怕,只怕还没来得及按自己的心意尽情活过,只是随波逐流,到站后方叹大梦初醒。只有不凡的人,才有资格,笑谈平凡是人生答案;庸常的人,说甘于平凡,不过是为无能找个借口。传统,只教我们处处”为别人活”,却不提”看重自我”。而岁月让我懂得,”好人”,在许多时候,就是失败和痛苦的根源。
人生走到这里,如果不努力也不改变,一眼看老,很多结局都呼之欲出了。无论你我,在走着怎样的路,惟愿那一条是你最想走的,而不是无奈之选。愿你有足够的勇气和担当,错了能回头,终了不遗憾。愿你倾心所爱之人,也同样爱着你。层林尽染叠翠流金之时,笑容不再孤单。
作者:OuTopos7
链接:http://www.jianshu.com/p/1711abc76879
來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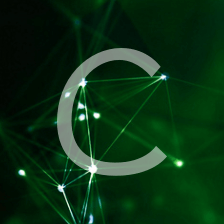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