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健
Review美国退役军人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的率及相关因素:一项叙述性综述
1. 引言
1.1. 背景
美国退役军人人口的估计规模约为2000万[1]。许多前服役人员可能会经历心理健康问题[2]。事实上,在一项针对超过30万名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的基于人群的大规模研究中,这些人员在从现役返回六个月后完成了部署后健康评估,其中13%的人员正经历重度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自杀或攻击性意念或人际冲突[3]。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VA)表明,美国退役军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增加,高达26%的退伍军人报告存在困难[4]。
先前的研究表明,有23%至40%符合精神健康困难标准的退役军人在需要时会使用心理健康服务[5]。影响这一群体寻求治疗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未能识别其精神健康障碍症状;认为自身症状不够严重;倾向于选择非正式而非正式的帮助资源;更愿意自行解决问题;担心产生不良职业后果;既往负面的治疗经历;获取服务方面存在困难;以及对与精神疾病相关的污名感到担忧[6–11]。
在寻求治疗的退役军人中,约有20%接受药物治疗或咨询[5,7],通常通过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即由医生或执业护士,或基于社区的服务提供。一项先前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大多数在此背景下寻求护理的退役军人往往处于失业状态,对心理健康持有负面信念,并伴有社会支持不足和日常生活功能较差[12]。虽然了解那些通过初级卫生保健迈出解决问题第一步的人群特征非常重要,但目前关于退役军人使用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即通常在治疗诊所或医院提供的更专业的专科治疗——的证据仍然缺乏。与仅停留在初级卫生保健的人群相比,使用二级心理健康服务或由初级卫生保健转介至这些服务的人通常具有更复杂的需求水平。目前,我们对利用二级心理健康服务的退役军人男女数量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知之甚少。
1.2. 目标
尽管已有针对现役美国军事人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寻求行为的综述,但据我们所知,尚无专门关注退役军人接受二级心理健康服务治疗的研究。为填补这一空白,我们对2001年至2018年间发表的、定量测量美国退役军人男女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情况的研究进行了叙述性回顾。本综述旨在确定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以及与该利用相关的因素。我们采用了叙述性综述设计而非系统性综述设计,以对该研究领域提供广泛且描述性的概述。
2. 材料与方法
2.1. 检索策略
我们检索了多个电子数据库,包括OVID医学文献数据库(Ovid 技术公司,纽约州纽约市,美国)、心理学信息数据库(美国心理学会,华盛顿特区,美国)、心理学文章数据库(美国心理学会,华盛顿特区,美国)和荷兰医学文摘数据库(爱思唯尔,阿姆斯特丹,荷兰),以识别报告退役军人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情况的英文论文。检索使用了以下关键词组合:退伍军人、军事人员、现役、士兵、服役人员、退役军人、前军事人员、武装部队、心理健康、心理福祉、精神障碍、寻求治疗、治疗使用、求助行为和服务使用。检索范围限定为2001年1月至2018年9月期间发表的文章,以便聚焦过去16年内的近期心理健康服务利用情况,并涵盖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整个时期(以及此后发表的相关论文)。同时,我们还检查了符合条件文章的参考文献列表,以查找其他符合本研究标准的论文。
2.2. 资格标准
本综述的纳入标准为:(1) 研究以量化心理健康服务利用作为其结果;(2) 研究聚焦于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定义为专科治疗,通常在治疗诊所或医院提供,包括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机构;以及 (3) 研究仅关注退役军人样本,其中大多数被纳入人员曾被部署到伊拉克和/或阿富汗的冲突中。
综述的排除标准为:(1) 综述、案例研究、会议记录、书籍、论文、学位论文以及对原始论文的评论/更正/回复;(2) 研究(包括随机对照试验)测试或调查特定临床干预措施的使用情况;(3) 重点关注非正式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的研究——定义为通过伴侣、家庭、朋友、同事或热线获得的支持;(4) 重点关注(前)军人特定亚群体的研究——特别是与性创伤或暴力、无家可归、刑事司法系统以及残疾索赔或补偿相关的研究。
3. 结果
共保留了15篇论文(见图1)。尽管我们检索了在任何国家开展的论文,但显然所有符合条件的研究均在美国进行。因此,我们缩小了本次综述的范围以符合这一美国重点,尽管这并非我们最初的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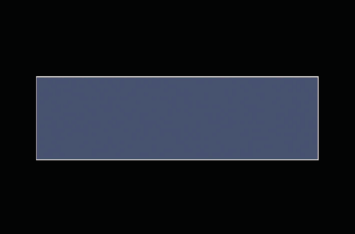
3.1. 研究特征
表1描述了所纳入的15项研究中的每一项的核心信息。所有研究均在美国进行,除一项外,其余均聚焦于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和诊所内的治疗[13]。退伍军人事务部是美国最大的综合性医疗保健系统,每年在1243个医疗机构为九百万退役军人提供服务[14]。这15项研究中有14项使用电子病历来识别退役军人的心理健康服务使用[15–28]。其中,八项研究回顾性地获取了医疗记录[16,22–28]。我们综述中的最后一项研究采用了横断面设计,参与者完成了自报测量[13]。
表1. 每个纳入的研究的核心信息。
| 参考文献 | N | 样本 | 结果 | 结果的时间范围 | 仅部署到阿富汗/伊拉克的样本 |
|---|---|---|---|---|---|
| Blais 等人 [15] | 173 | 患有PTSD的退役军人,注册于退伍军人事务部部署后诊所用于初步评估。 | 是否出勤两次或以上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用于个体心理治疗、团体心理治疗,以及精神科就诊。 | 12个月,初次评估之后 | 是 |
| 德维瓦 [16] | 200 | 患有PTSD的退役军人,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专科医生处的门诊诊所。 | 是否参加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仅针对心理治疗疗程。 | 无时间段规定 | 是 |
| DeViva 等人 [17] | 97 | 患有PTSD的退役军人,心理健康服务在某一时间段内。 | 是否参加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仅限心理治疗疗程。 | 六个月,转诊后至诊所 | 是 |
|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 | 137 | 退役军人,在初次评估时预定的筛查在一个特定的预约退伍军人事务部门诊诊所。 | 是否参加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 | 12个月,初次评估之后 | 是 |
| 赫恩 [19] | 429 | 患有任何DSM一级轴障碍的退役军人,注册于退伍军人事务部部署后诊所进行初步评估。 | 是否参加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 | 12个月,初次评估之后 | 是 |
| Hoerster 等人 [20] | 305 | 患有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或酒精滥用,注册了退伍军人事务部部署后诊所进行初步评估。 | 出勤九次或以上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的是/否,符合最低适当的治疗。 | 12个月,初次评估之后 | 是 |
| 哈德森等人 [21] | 4782 | 退役军人,在首次预约时于一个退伍军人事务部门诊诊所。 | 是否参加门诊心理健康护理,仅针对心理治疗疗程的护理访问。 | 三个月,初次评估之后 | 是 |
| Kaier 等人 [22] | 124 | 患有PTSD或酒精滥用的退役军人,由初级保健提供者或退伍军人事务部个案管理团队。 | 是否参加门诊心理健康护理 | 六个月,转诊之前 | 是 |
| Koo 等 [23] | 309,050 | 患有PTSD、抑郁症、焦虑症,适应障碍,或酒精或药物使用障碍的退役军人,进入退伍军人事务部护理。 | 是否参加门诊心理健康护理,以及精神科住院时间。 | 12个月,初次评估之后 | 是 |
| 马古恩等人 [24] | 159,705 | 患有PTSD的退役军人,在首次预约评估时于退伍军人事务部门诊诊所。 | 是否参加门诊心理健康护理,以及精神科住院时间。 | 12个月,初次评估之后 | 是 |
| McGinn 等人 [25] | 130 | 处于稳定关系中的退役军人,注册于退伍军人事务部部署后诊所用于初步评估。 | 心理健康护理就诊出勤的是/否,用于门诊精神科和心理治疗疗程。 | 12个月,初次评估之后 | 是 |
| 纳拉贡‐盖尼等人 [26] | 618 | 退役军人,在首次预约时于一家退伍军人事务部门诊诊所。 | 心理健康就诊次数,用于心理健康与初级医疗就诊、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以及精神科住院停留。 | 24个月,初次评估之后 | 是 |
| 惠林等人 [13] | 233 | 退役军人来自夏威夷,通过识别一个伊拉克/阿富汗时代退役军人项目名册。 | 心理健康护理就诊出勤的是/否,用于退伍军人事务部心理治疗疗程,退伍军人事务部心理健康护理就诊,以及社区心理健康护理就诊。 | 三个月,进入研究前 | 是 |
| 凯尔‐福布斯等人 [27] | 427 | 患有PTSD的退役军人,被提及到,参加在初步评估时,以及提出以供进一步在某一特定退伍军人事务部门诊诊所接受治疗。 | 是否参加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 | 36个月,转诊后到诊所 | 是 |
| 凯勒和特克[28] | 324 | 患有PTSD的退役军人,在初步评估中接受评估,在一次特定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门诊诊所,提供心理治疗,以及指派一名治疗师以开始。 | 是否参加门诊心理健康护理,进行基于证据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 | 8个月,以下在诊所。 | 是 |
N=目标研究中的参与者数量;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VA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DSM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每项研究的平均受访者人数为31,782人(范围 = 97[17]–309,050[23])。所有论文的样本均为混合性别,尽管女性通常仅占参与者的较小比例(在15项研究中平均为10.7%;范围 = 3.6%[18]–23.0%[28])。这一较低比例反映了女性enlisted人员仅占美国军队前线部队的2.7%。其中13项研究招募了仅在伊拉克和/或阿富汗服役过的退役军人[13,15–26]。在纳入的15项研究中,有10项研究招募了临床样本——即由具有临床诊断/多种诊断并曾就诊于心理健康服务的参与者组成的样本[15–17,19,20,22–24,27,28]。其余5项研究中,3项包括参加初次心理健康评估预约的个体[18,21,26];1项包括参加强制性部署后筛查诊所的个体[25];还有1项包括来自社区并通过退役人员项目名册确定的个体[13]。
3.2. 测量
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的操作化在各论文中有所不同。八项研究仅将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包括心理治疗预约和精神科预约)作为其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的测量指标[15,16,18–20,25,27,28]。十一篇论文同时采用了分类的——对心理健康服务利用情况进行二分的是/否分类——以及连续的——心理健康服务参与度次数——这两种在给定时间段内衡量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的指标[15–18,20–25,27]。七项研究使用了12个月时间段来测量心理健康服务利用情况[15,18–20,23–25]。
3.3. 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
为了确定不同测量方法和操作化定义下的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结果被分为六个类别(见表2)。这六个类别由上述段落中列出的两种测量差异的二乘三组合构成——(1) 二分法与连续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结果(两个水平);以及 (2) 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住院精神病医院停留和药物使用(三个水平)。因此,这六个类别分别为:(1) 二分的,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结果;(2) 二分的,住院精神病医院停留结果;(3) 二分的,药物使用结果;(4) 连续的,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结果;(5) 连续的,住院精神病医院停留结果;以及 (6) 连续的,药物使用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研究的结果涉及这六个类别中的多个类别。
表2. 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
| 分类 | 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 | 住院精神病医院停留 | 心理健康药物使用 |
|---|---|---|---|
| 二分的 | |||
| 参考文献 | 比率 (%) / 编号 | 参考文献 | 比率 (%) / 编号 |
| Blais 等人 [15] | 90% * | Koo 等人 [23] | 13% |
| 德维瓦 [16] | 62% | 马古恩等人 [24] | 12% |
| 德维瓦等人 [17] | 33% | ||
|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 | 73% | ||
| Hoerster 等人 [20] | 25% * | ||
| 哈德森等人 [21] | 52% | ||
| Kaier 等人 [22] | 68% | ||
| 凯尔‐福布斯等人 [27] | 82% | ||
| Koo et al. [23] | 93% | ||
| 马古恩等人[24] | 96% | ||
| McGinn 等人[25] | 50% * | ||
| 惠林等人[13] | 36% | ||
| 总体平均比率 | 63.2% | 12.5% | |
| 连续的 | |||
| 参考文献 | 率 | 参考文献 | 率 |
| Blais 等人 [15] | 8.6 | Koo 等人 [23] | 0 |
| 德维瓦 [16] | 7.0 | 马古恩等人 [24] | 0.1 |
|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 | 14.7 * | 纳拉贡‐盖尼等人 [26] | 0.1 |
| Kaier 等人 [22] | 7.8 | ||
| Koo et al. [23] | 2.2 | ||
| McGinn 等人 [25] | 6.6 | ||
| 纳拉贡‐盖尼等人 [26] | 7.6 | ||
| 总体平均率(标准差) | 7.9(12.7) | 0.1 (0.4) |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标准差 =标准差。‘率’值表示:类别(1)指在研究的样本和时间段内,至少接受一次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的退役军人的百分比患病率;类别(2)指在研究的样本和时间段内,至少经历一次精神科住院治疗的退役军人的百分比患病率;类别(3)指在研究的样本和时间段内,被开具药物处方的退役军人的百分比患病率;类别(4)指在研究的样本和时间段内,退役军人接受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的平均次数;类别(5)指在研究的样本和时间段内,退役军人精神科住院治疗的平均次数;类别(6)指在研究的样本和时间段内,退役军人服药天数平均值。* 表示对上述‘率’定义的例外情况:对于类别(1),Blais 等人 [15]报告的是接受两次或以上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的退役军人的患病率,Hoerster 等人 [20]报告的是接受九次或以上就诊的退役军人,McGinn 等人 [24]报告的是接受一次或两次就诊的退役军人;对于类别(4),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报告的是至少接受过一次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的退役军人的平均就诊次数——而其他研究报告的是整个退役军人样本(包括接受过治疗和未接受过治疗者)的平均就诊次数;对于类别(6),Kaier 等人 [22]报告的是在六个月内该特定样本中服药天数,即服药天数。注:247 的数值大于 182.5(六个月内的天数),因为在同一天服用两种不同类型的药物时计为两天。
对于类别(1)——二分的,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在14项具有相关数据的研究中,至少进行一次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的平均百分比患病率为63.2%,平均时间段为10.4个月[13,15–25,27,28]。
对于类别(2)——二分的,住院精神病医院停留——在两项具有相关数据的研究中,至少经历一次精神科住院治疗的平均百分比患病率为12.5%,平均时间段为12个月[23,24]。
对于类别(3)——二分的,药物使用——在四项具有相关数据的研究中,被开具药物的平均患病率为43.5%,平均时间段为4.5个月[13,17,19,20]。
对于类别(4)——连续的,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在11项具有相关数据的研究中,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的中位数次数为7.6次,平均时间段为13.1个月[15–18,20,22–27]。
对于类别(5)——连续的,住院精神病医院停留——在三项具有相关数据的研究中,住院精神病医院停留的中位数次数为0.1次,平均时间段为16个月[23,24,26]。
最后,对于类别(6)——连续的,药物使用——在一项具有相关数据的研究中,服药天数为247天,时间段为六个月[22]。
3.4. 相关因素
表3–5分别展示了与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相关的心理健康因素、社会人口学、军事人员和人格因素,以及治疗和功能因素。
表3. 每个纳入的研究中与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相关的心理健康因素,以及关联方向。
| 相关因素 | 显著正向关联 | 无显著关联 | 显著负向关联 | 心理健康因素 |
|---|---|---|---|---|
| PTSD严重程度 | 德维瓦等人 [17]¹,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¹, Hoerster 等人 [20]¹, McGinn 等人 [25]⁴, 纳拉贡‐盖尼等人 [26]⁴,⁵, 惠林等人 [13]¹, 凯尔‐福布斯等人 [27]¹, 凯勒和特克 [28]¹ | |||
| 回避型集群 |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¹ | Kaier 等人 [22]⁴,⁶ | Blais 等人 [15]⁴ | |
| 抑郁集群 | Blais 等人 [15]⁴ | |||
| 过度警觉集群 | Blais 等人 [15]⁴ |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¹ | Kaier 等人 [22]⁴,⁶ | |
| 麻木集群 |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¹ | |||
| 再体验集群 | Blais 等人 [15]⁴ |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¹ | Kaier 等人 [22]⁴,⁶ | |
| 抑郁症 | Hoerster 等人 [20]¹, 马古恩等人 [24]⁴,⁵ |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¹,⁴, Kaier 等人 [22]⁴,⁶, 纳拉贡‐盖尼等人 [26]⁴,⁵ | 德维瓦 [16]¹ | |
| 物质使用障碍 | 德维瓦 [16]¹ | 赫恩 [19]¹ | ||
| 酒精使用障碍 | 马古恩等人 [24]⁴,⁵ | 赫恩 [19]¹, Kaier 等人 [22]⁴,⁶, 纳拉贡‐盖尼等人 [26]⁴, 惠林等人 [13]¹ | ||
| 创伤性脑损伤 | 德维瓦 [16]¹, 惠林等人 [13]¹ | |||
| 共病 | 赫恩 [19]¹, 马古恩等人 [24]⁴,⁵ | |||
| 痛苦 | Kaier 等人 [22]⁴,⁶ | |||
| 攻击性 | 纳拉贡‐盖尼等人 [26]⁴ | |||
| 恐慌 | 纳拉贡‐盖尼等人 [26]⁴ |
注:上标数字(1–6)代表类别组合:(1) 二分的,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结果;(2) 二分的,住院精神病医院停留结果;(3) 二分的,药物使用结果;(4) 连续的,门诊心理健康护理就诊结果;(5) 连续的,住院精神病医院停留结果;(6) 连续的,药物使用结果。
表4. 每个纳入的研究中与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军事和人格因素,以及关联方向。
| 相关因素 | 显著正向关联 | 无显著关联 | 显著负向关联 | 社会人口学因素 |
|---|---|---|---|---|
| 女性性别 | Blais 等人 [15]⁴, 德维瓦 [16]¹, Hoerster 等人 [20]¹, 赫恩 [19]¹, 哈德森等人 [21]¹,³, 凯尔‐福布斯等人 [27]¹, 凯勒和特克 [28]¹, 马古恩等人 [24]⁵, 惠林等人 [13]¹ | |||
| 白人种族 | Blais 等人 [15]⁴, 德维瓦 [16]¹, 赫恩 [19]¹, 哈德森等人 [21]¹,³, 凯勒和特克 [28]¹, 惠林等人 [13]¹, Koo et al. [23]¹,² | |||
| 高龄 | 德维瓦 [16]¹, 凯尔‐福布斯等人 [27]¹, 凯勒和特克 [28]¹ | 赫恩 [19]¹, 哈德森等人 [21]¹,³, 惠林等人 [13]¹ | ||
| 婚姻状况 | 德维瓦 [16]¹, 惠林等人 [13]¹ | |||
| 就业状况 | 德维瓦 [16]¹ | |||
| 非学生身份 | 德维瓦 [16]¹ | |||
| 更高的教育水平 | 惠林等人 [13]¹,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⁴ | |||
| 城市居住地 | 哈德森等人 [21]¹, 惠林等人 [13]¹ | |||
| 为人父母 | Kaier 等人 [22]⁴,⁶ | |||
| 更高的年收入 | McGinn 等人 [25]⁴ | |||
| 军事因素 | ||||
| 战斗暴露 | Blais 等人 [15]⁴,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¹ | |||
| 经历的创伤次数 | 赫恩 [19]¹ | |||
| 军人身份(现役与预备役) | Blais 等人 [15]⁴, 德维瓦 [16]⁴ | |||
| 服役部门 | Hoerster 等人 [20]¹ | |||
| 自上次部署以来的时间 | 赫恩 [19]¹, 德维瓦 [16]¹ | |||
| 部署次数 | 德维瓦 [16]¹ | |||
| 服役关联 | 哈德森等人 [21]¹,³ | |||
| 单位社会支持 |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¹ | |||
| 部署后社会支持 | DeViva 等人 [17]¹,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¹ | |||
| 作战时代 | 凯勒和特克 [28]¹ | |||
| 担心失去基于军事的警觉性 |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¹ | |||
| 人格因素 | ||||
| 人格 | 德维瓦等人 [16]¹ | |||
| 韧性 | 德维瓦等人 [17]¹,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¹,⁴ |
表5. 每个纳入的研究中与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相关的治疗和功能因素,以及关联方向。
| 相关因素 | 显著正向关联 | 无显著关联 | 显著负向关联 | 治疗因素 |
|---|---|---|---|---|
| 药物使用 | 德维瓦 [16]¹ | |||
| 对心理健康护理的积极信念 | DeViva 等人 [17]¹ | |||
| 心理健康护理的障碍 | Hoerster 等人 [20]¹ | |||
| 关于心理健康护理的污名 | DeViva 等人 [17]¹, Hoerster 等人 [20]¹, 惠林等人 [13]¹ | |||
| 治疗机构类型 | 哈德森等人 [21]¹,³ | |||
| 转诊机构类型 | 凯勒和特克 [28]¹, 德维瓦 [18]¹ | |||
| 治疗的提供 | 凯尔‐福布斯等人 [27]¹ | |||
| 治疗类型 | 凯尔‐福布斯等人 [27]¹ | |||
| 治疗提供者的培训水平 | 凯勒和特克 [28]¹ | |||
| 在退伍军人事务部以外接受治疗的参与情况 | 赫恩 [19]¹ | |||
| 表达在退伍军人事务部以外接受治疗的兴趣 | 赫恩 [19]¹ | |||
| 到最近的退伍军人事务部诊所的距离 | 惠林等人 [13]¹ | |||
| 功能因素 | ||||
| 法律问题 | 德维瓦 [16]¹ | |||
| 社交障碍 | Kaier 等人 [22]⁴,⁶ | |||
| 关系满意度 | McGinn 等人 [25]⁴ | |||
| 职业功能障碍 | Kaier 等人 [22]⁴,⁶ | |||
| 睡眠质量 |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¹ | |||
| Pain | 德维瓦 [16]¹, 纳拉贡‐盖尼等人 [26]⁴,⁵ | |||
| 生活质量 | 惠林等人 [13]¹ | |||
| 生活满意度 | 哈尔帕兹‐罗特姆等人 [18]¹ |
如表3所示,最常报告的统计学显著关联(在八项研究中的六项中报告)是PTSD严重程度与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之间的关联[13,17,18,20,25,26]。PTSD更严重的个体中治疗利用发生得更频繁。当PTSD按子量表划分时,只有再体验症状子量表与服务利用相关。三项(共三项)研究报道了再体验症状与治疗利用之间的正向关系[15,18,22]。
关于抑郁症与治疗利用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不一——两项研究报道了正向关联[20,24],一项报道了负向关联[16],三项报道了无统计学显著关联[18,22,26]。酒精使用障碍这一心理健康诊断的支持证据也较少。一项研究中其与医疗利用呈正向关联[24],四项研究中与医疗利用无统计学显著关联[13,19,22,26]。利用情况与共病显著相关,在两项(共两项)研究中发现了正向关系[19,24]。
如表4所示,年龄对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的影响尚不明确。高龄在三项研究中与利用呈正相关[16,27,28],在另外三项研究中与利用无显著关联[13,19,21]。性别和种族这两个社会人口学变量的情况亦是如此。女性性别和白人种族分别在两项研究和一项研究中与心理健康服务利用呈正相关。这些因素分别在零项研究和一项研究中与心理健康服务利用呈负相关。然而,七项检验性别关联的研究[13,16,19,24,27,28],以及五项检验种族关联的研究[13,16,19,21,28]均未发现这些构念与治疗利用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因此,这些因素的结果尚不明确。
除了上文已讨论的因素外,如表3–5所示,还考察了其他一系列心理健康、社会人口学、军事人员、人格、治疗和功能因素。这些额外因素均未显示出与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存在一致的关联。
4. 讨论
4.1. 主要发现
本叙述性综述发现,在纳入的15项研究中,美国退役军人的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较低,表明其寻求治疗的程度适中。各研究中心理健康服务利用频率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可归因于纳入研究在利用定义和操作化方式上的显著不同,以及样本招募方法的差异。
两项主要因素被证实始终与较高的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水平相关:创伤后应激障碍(尤其是再体验症状)和共病。其他一些因素在服务使用方面的结果则呈现不一致,其中最令人意外的是抑郁症症状和年龄。
4.2. 与先前研究的比较
本综述发现的心理健康治疗利用率与以往针对退役军人群体的研究所报告的结果相似。例如,有一篇论文报告称,在部署到伊拉克或阿富汗后的第一年内,平均有33%的美国退役军人使用了住院和门诊心理健康服务[3]。在考虑美国平民人群中的寻求治疗情况时,也发现了相当的率[28–31]。鉴于某些面临服务参与障碍的社会经济群体(例如年轻男性以及来自较低社会经济群体的个体)在军事人员中比例较高,我们可能会预期军事人员中的治疗利用率较低[32]。然而,由于该群体属于心理健康困难的高风险人群,因此也可以说他们应比普通人群更愿意寻求帮助[8]。
如前所述,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的率因所使用术语的操作化定义不同而有所差异。大多数现有研究在关注现役和退役军人的治疗利用时,将初级和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合并在一起[6–8,22,33],这使得难以分别评估不同类型求助行为的率。霍格及其同事在美国开展的一项研究是个例外,该研究区分了初级和二级护理,并报告称,纳入的军事人员样本中有28%曾使用过二级门诊心理健康诊所[5]。这一数字明显低于本综述中接受二级门诊心理健康就诊者的平均百分比患病率63%。霍格及其同事的研究对象是部署到伊拉克或阿富汗后的服役人员——其中部分已退役,部分仍在服役;而本综述仅关注退役军人[5]。我们了解到,已不再服役的人员相较于仍在服役者,更倾向于寻求针对抑郁症、焦虑症和酗酒问题的心理健康治疗[8,34],这可能提高了本综述中求助行为的率。此外,霍格及其同事招募的是基于人群的军事样本,这些人员完成了常规的部署后健康评估[5];而我们纳入的研究主要从退伍军人诊所招募参与者,且侧重于那些已经表现出寻求治疗行为的个体。
4.3. 相关因素
在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增加的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之间发现的主要一致关联,与以往关于精神卫生服务使用情况的研究结果一致[35]。这种关系可以说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与较高的功能损害率相关,从而需要比初级保健环境所提供的支持更高级别的照护。最近研究退役军人心理健康护理使用的预测因素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严重程度越高,服务使用越多[36,37]。心理健康问题负担较重的退役军人对心理健康护理的需求更大,因此更有可能寻求治疗[36]。然而,本次综述中的两项研究并未支持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心理健康服务利用之间的关联[27,28]。这两篇论文均包括最后部署至伊拉克、阿富汗或其他地点的人员,而其他13篇论文所涉及的样本仅限于最后部署至伊拉克和/或阿富汗的人员。或许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伴随症状的表现因作战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进而导致在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方面产生不同的反应。
本综述发现,当测量进一步细分时,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再体验症状与更高水平的寻求治疗相关。由于再体验症状与部署期间的创伤提醒有直接关联,可能有助于退役军人和医疗保健提供者认识到当前的痛苦是由创伤后应激障碍引起的,从而促进更多地使用心理健康服务[13]。相比之下,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其他症状(如情绪低落或过度警觉)可能会被归因于心理社会问题——例如人际关系困难;重新适应问题——例如在部署期间形成的睡眠习惯;或医学问题——例如肌肉骨骼疼痛[13]。
在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与心理健康诊断的共病之间发现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在现有文献中已有充分证实[38,39]。海因斯及其同事报告称,符合两种或以上心理健康问题标准的现役和退役军人,相较于不符合或仅符合一种问题标准者,其心理求助行为水平更高[40]。精神疾病共病可被视为患者痛苦的替代指标[40],并且如前所述,随着退役军人的痛苦程度及其治疗需求的增加,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心理健康治疗。
出乎意料的是,抑郁症与求助行为之间并未表现出显著关联。波塞马托及其同事早前的研究发现,抑郁症等心理健康状况与退役军人门诊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增加之间存在关联[39]。本综述所纳入的研究仅关注那些因心理健康问题而寻求帮助的个体。而先前论文中所包含的退役军人,则是因心理健康困难或身体健康困难而寻求帮助[39]。已有研究表明,同时患有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且日常生活功能较差的个体,比仅有心理健康问题且功能较好的个体更频繁地获取心理健康治疗服务[6,41]。
本综述揭示了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与年龄之间关联的混合结果。这与以往文献一致,表明年龄与该关系尚不明确。例如,一项研究发现,高龄与伊拉克和阿富汗退役军人的更高治疗参与度相关[41]。另一篇论文发现,在首次筛查出创伤后应激障碍阳性时,30岁以下的退役军人比30岁以上的退役军人更可能获得心理健康治疗[42]。还有更多研究发现,年龄与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之间无显著关联[33]。所报告的不一致关联可能由第三个中介变量解释——例如,多篇论文发现,年龄的影响可由精神疾病数量、创伤暴露次数、退役后的月数以及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内的不同心理健康诊断率来解释[19,43]。
4.4. 优势与局限性
这项针对美国退役军人二级心理健康服务利用情况的定量测量、全面多数据库叙述性检索与综述采用了严谨且成熟的方法论。然而,考虑到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的操作化定义存在差异,我们使用平均患病率和平均数量来测量参与度的比率,在所纳入的研究之间可能不具备可比性。在涉及的15篇论文中,所有研究均在美国进行,且均仅包含少数女性。因此,这些论文中检测性别与寻求治疗之间关联的统计功效可能有限;但人数较少的情况反映了在美国军队中实际服役以及在战斗中阵亡的女性所占百分比较低。然而目前,女性是美国退伍军人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未来的研究应更深入地探讨这一特定亚群体的心理健康服务利用情况。尽管少数研究依赖于自报测量的治疗利用数据,但有11项研究使用了电子健康记录登记系统。这些登记系统的优势在于能够为大量参与者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多个测量时间点[44]。另一方面,电子系统的局限性包括通常存在大量缺失数据[45,46],非标准化临床自由文本记录[46,47],以及缺乏关于未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的信息[48]。
4.5. 意义与结论
本文提供的证据表明,退役军人对二级心理健康服务的治疗利用水平适中。个体最常进行门诊护理就诊,很可能是因为这类预约是最常见的支持来源。我们的结果与先前报道的现役人员和平民人群寻求二级心理健康服务的情况相似。二级心理健康服务的利用主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再体验症状以及更多的共病精神障碍相关。对于年龄、性别和抑郁症等因素,其与二级心理健康服务的关系表现出不一致的关联,仍需进一步研究。此外,我们建议开发易于获取的干预措施(例如移动健康工具),以促进退役军人求助行为率的显著提高。研究的总体目标必须始终是有效减少令人痛苦的、具有临床意义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具体而言,将患有非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关诊断的退役军人与心理健康治疗相连接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被折叠的 条评论
为什么被折叠?








